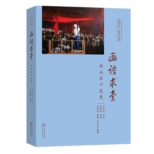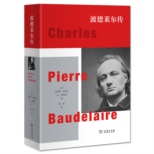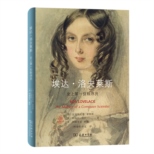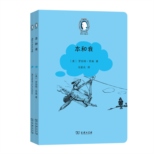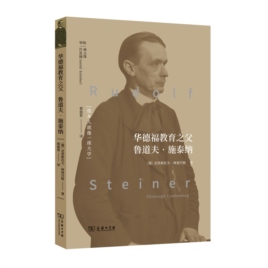鲁道夫·施泰纳(Rudolf Steiner)出身贫困,却从不以此大作文章,顶多是顺带一提生长环境的拮据状况。然而,在1919 年的一场学术讨论会上,曾有某位对困顿生活一无所知的人,道听途说地针对邮局小职员的生活情况大肆评论,使他按捺不住:“……我对无产阶级的认识是怎么来的,正因为我自己就是过着无产阶级的生活,我就是在无产阶级的生活环境下被抚养长大,从无产阶级所过的日子里懂得什么叫挨饿,而且也不得不饿肚子。” 相较同样出生于1960 年代奥匈帝国(Donaumonarchie)的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马勒(GustavMahler,1860)、赫茨尔(Theodor Herzl,1860)、施尼茨勒(ArthurSchnitzler,1862)、巴尔(Hermann Bahr,1863)等人,施泰纳的出身背景在他与这群享誉盛名或知名艺文人士之间画出一道清晰的界线。这些文人雅士无不来自中产阶级家庭或是上流社会,他们自然而然地在奥匈帝国晚期艺文教育的熏习之下成长。有些人甚至就读一流的维也纳中学,该校传授学子当时具美学观的知性文化,更进而滋养了维也纳当代潮流(Wiener Moderne),发展出丰硕多元的文化果实。反观施泰纳家族,毫无值得一提的文化传统,家中没有书架,更别说是书柜。由于施泰纳的父亲对宗教的态度自由开放,宗教在这个家庭中同样显得无足轻重。施泰纳即是在这般既无优势也无阻力的环境中长大成人。
施泰纳一直到十八岁都生活在乡下地区,却不能算是乡下小孩。由于父亲在铁路局上班,必须经常调派到各地,以致施泰纳对乡下的环境难以产生归属感。十岁时的他早已感
受到自己是“镇上的外来者” ,无法融入当地的生活圈,一座又一座的火车站成了他童年回忆的所在。对周遭环境的兴致使然,他更逐渐专注于铁路的作业上头:“铁路的整个组织运作让我忙得不可开交。一开始,我通过观察车站的电报机认识了电学的原理,就连打电报也早在还是小男孩时就学会了。后来即便到了邻近城市的学校上课,身为“外来者”的他仍然没办法和班上的同学打成一片,在乡下更是格格不入。
因此,他在自传《我的生命历程》(Mein Lebensgang)中,从未提及求学时期的朋友或是恶作剧等事情。他的一位同学回忆道:“我们这群人搞出种种荒唐的恶作剧,还因而受罚,他当然不曾沾上边。”
早在父亲约翰·施泰纳(Johann Steiner,1829—1910)放弃内心向往的猎人与樵夫工作,决定前往异地寻求他的机遇以便能和弗兰齐斯卡·布利(Franziska Blie,1834—1918)结婚时,这种疏离和居无定所的感觉即已开始滋长。约翰·施泰纳在奥地利帝国南部铁路公司找到一份报务员的职位,并于 1861 年 1 月初被派往位于今克罗地亚境内的克拉利耶维奇(Kraljevec)。1861 年 2 月 25 日,鲁道夫·施泰纳在这远离亲友家人的偏远乡村诞生了。两天后,即 2 月 27 日,他在一般认定为其诞生日的那天受洗。最初的几年,鲁道夫通常由极其沉默寡言的母亲独力照顾,当时他的父亲必须三天三夜不眠不休地值班,才得以轮休二十四小时,气力早已消耗殆尽。1862 年,他的父亲被调到默德林(Mödling)。
1863 年初,又被调任至波特夏赫镇(Pottschach)的森默林铁路公司(Semmeringbahn)担任站长职务,于是这个位于施瓦察河(Schwarza)景致宜人的河谷中的小镇便成了施泰纳儿时的乐园。施泰纳的妹妹莱奥波尔迪娜·施泰纳(Leopoldine Steiner,1864—1927)和弟弟古斯塔夫·施泰纳(Gustav Steiner,1866—1941)陆续在此地出生;施泰纳的父母和磨坊的居民发展出友善的邻里关系;附近小镇圣瓦伦廷(St. Valentin)的神父,举止犹如波特夏赫镇“德高望重的绅士”般,是个热衷于关注火车到站与离站情形的独特之人。当施泰纳欢愉地忆及那山间景致, 雪山(Schneeberg)、雷克斯阿尔卑斯山脉(Raxalpe)以及威悉泽山(Wechsel),分别从南面、西面及北面环抱着山谷,回想起山谷中的田野、
矮树篱和森林,那儿可说是“奥地利国境内最美的小镇之一”。
在波特夏赫镇的幸福时光持续了六年,接着施泰纳的父亲就被调往维也纳新城(Wiener Neustadt)附近的诺伊多弗镇(Neudörfl)。施泰纳家又过起封闭的生活,与镇上的人们并没有值得一书的来往互动。施泰纳的弟弟古斯塔夫既聋又哑,智力发育不完全,需要长期照护,成为这个家庭共同的忧苦,施泰纳一家人因而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要从这种环境跳脱出来的最佳途径,就是教育。
关于求学,早在波特夏赫镇就完全由他的父亲全权决定。“我的父亲盘算着让我早点去学阅读写字,一到义务教育规定的就学年龄,就把我送到村里的学校上课。” 施泰纳的父亲也相当重视孩子的受教质量,施泰纳上学几周后,因为背黑锅而必须遭到惩处,父亲毅然决然地为他办理退学,并于公务之余亲自教导。在诺伊多弗镇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形:“在担任‘辅祭童’期间,我必须协助弥撒圣祭、下午礼拜、丧礼、基督圣体节等仪式的进行。早上好几位辅祭童,包括我在内,在担任辅祭工作时迟到。在这所学校,这些迟到的学生全都得遭受体罚。我当时对这种做法厌恶到极点,懂得躲避体罚,总是能适时躲开,所以从没被体罚过。不过我父亲一想到‘他的孩子’必须被体罚就暴跳如雷,他说:‘这些教会辅祭的事情到此为止,不准再去。’于是这个辅祭工作就这么突然地画下句点。”在诺伊多弗镇期间,施泰纳的父亲亲自为他的孩子和村里的其他男孩上“特别辅导课”。后来,约翰·施泰纳还让他的孩子去维也纳新城较高等的学校就读。这对这个家庭而言不仅困难重重,在他们的生活圈也是相当不寻常的事情。最后,父亲总算再次顺利为他的儿子申请到专为奥地利帝国南部铁路公司职员子女而设的奖学金,资助鲁道夫·施泰纳到维也纳理工学院求学。鲁道夫·施泰纳倒也不是对所有的事情都完全不参与,他善用自身拥有的机会,尽管对未来的职业生涯发展没有帮助,却能激发求知欲与学习热忱。正因如此,鲁道夫升上三年级以后便成为“优秀生”,这意味着他的父母不需再缴纳学费。从 1876 年 10 月起,施泰纳必须定时教授辅导课,也因此他才能够得到“多少补贴一些父母资助我求学的微薄收入。”不过这堂辅导课对施泰纳本身也是意义重大:“我由衷地感谢这堂辅导课。我在课堂上将所学内容去教导他人的同时,或多或少也激发了自身对这门科目的兴趣。毕竟,我所能教导的,除了在课堂上如置身梦境般学来的知识,别无其他。”施泰纳总算没有辜负父母的付出,不仅毕业考取得“优等”的优异成绩,更达到申请奖学金的标准。与其说鲁道夫是他人眼中勤勉求学的好学生,某种程度而言,他更扮演着自己的良师。若是“自学者”(Autodidakt)一词没有掺杂其他贬低的意味,那么说鲁道夫·施泰纳是孜孜不倦的自学者再贴切不过。很早以前,他的手里就已经捧着吕布森(Hinrich Borchert Lübsen,1801—1864)专为微积分学自修者所写的书,再加上勤于练习演算,所以一进入维也纳理工学院,他的数学掌握程度就大幅领先其他学生。他的速记也同样是无师自通,根据同学的说法,施泰纳简直就是速记员,任何一位老师的讲话速度都跟得上。学校的历史课枯燥乏味,所以施泰纳在旧书店买了冯·罗特克(Karl von Rotteck, 1775 —1840)的《世界通史》(AllgemeineWeltgeschichte),还另外买了约翰内斯·冯·缪勒(Johannesvon Müller, 1752—1809)和塔西佗(Tacitus, A.D.55—A.D.120)的著作。火车站驻站医师希克尔(Carl Hickel)借给他的德国古典戏剧,他读得十分入迷。当他发现他的德文老师相当尊崇哲学家赫尔巴特(Johann Friedrich Herbart,1776—1841),他便设法取得研究赫尔巴特的学者林德纳(Gustav Adolf Lindner)的著作《经验心理学概论》(Lehrbuch der empirischen Psychologie),这本书当时在奥地利相当热门,更是将弗洛伊德带入心理学领域的推手,而施泰纳在写作中大量使用相关术语,令这位老师颇为恼怒。施泰纳如何看待他在青少年阶段的学习,从他的自传可一窥究竟。
他在书中对于老师的详尽描述远胜于描述自己的父母,师长群像可从波特夏赫镇学校那位垂垂老矣的老师开始说起。在那位老师的眼里,“课堂管理是件麻烦事”;接着是诺伊多弗镇的辅导老师甘格尔(Heinrich Gangl),他是一位有天分的插画家,曾教导施泰纳画画;最后提到了维也纳新城理科中学的老师们。对于数学和物理老师,他最是推崇备至,“他的课程讲解条理极为分明又浅显易懂”。数学老师是施泰纳在数学思考上的理想和典范。他也相当赞赏他的几何学老师,“因为他,使用圆规、直尺和三角板成了我最喜爱的练习”。化学老师是“一位非常出色的人。他讲解不多,几乎都是以带实验的方式上课,让自然现象亲自现身说法”。他的自传中只字未提糟糕透顶的外语课和自然史,倒是用了几段更
长的段落描述那位合不来的“聪明绝顶的教授” 。从这些描述中我们可以拼凑出,在维也纳新城理科中学的求学期间,施泰纳在数学与精确的自然科学方面获得绝佳的启发。相形之下,文学、历史(最后一年的历史课除外)、语言和生物等科目则是一团糟。“不过,在上这些课的时候,我努力利用这几门课以外所学的内容来提振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