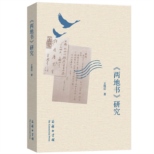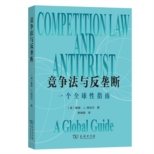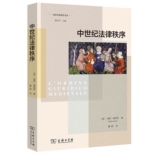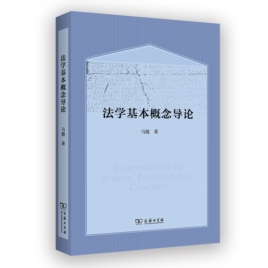专研法学基本概念,重构法学基本概念群。
法学基本概念,又称基本法律概念、基本法律范畴,是法理学所专门关注的针对法律一般性质的、普遍性的、基础性的概念。本书是针对法律渊源、法律效力、法律规范、法律权利、法律义务、法律主体、法律行为等典型的法学基本概念,在法理学的学科视野内开展的专门研究。与学界已有的研究相比,本书力图站在不涉及实质价值判断的立场,摆脱学术史的桎梏,借助当代分析法理学的理论资源,初步重构出一套体现法律基本性质的、超越特定部门法的法学基本概念群。
导 论
本书是对权利、义务、法律主体、法律规范、法律渊源、法律行为等法学基本概念(juristic foundational concepts)的专门研究。稍稍回顾中外学术史便不难发现,法学基本概念是中外法理学(jurisprudence)研究中的基础内容和重要组成部分。在英美分析法理学传统中,从边沁(Jeremy Bentham)开始,奥斯丁(John Austin)、格雷(John Chipman Gray)、萨尔蒙德(John W. Salmond)、霍菲尔德(Wesley Newcomb Hohfeld)等知名作者的重要法理学论著均包含大量针对法学基本概念的分析,一些著述甚至就是以法学基本概念为主要内容或核心的。二战后,哈特(H. L. A. Hart)、德沃金(Ronald Dworkin)、拉兹(Joseph Raz)等人的著述同样包含对法学基本概念的分析。德语世界中,在法尔克(Andreas Funke)、默克尔(Adolf Merkel)等人看来,一般法学说的任务在于认识内在于实在法中的普遍和不变的要素,探索被立法预设为前提的法律关系的本质,同时形成有普遍法律意义的基本概念。在其影响之下,凯尔森(Hans Kelsen)更是建构了现代法律语境中的法学基本概念体系。在中国学界,法理学的研究和教学同样关注法学基本概念。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法理学研究,基本上继受了苏联国家与法的一般理论,法学基本概念是其中的重要内容。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法学基本概念的研究成为中国理论法学复兴和发展的重要起点,法理学教材的内容长久以来均以法学基本概念体系为框架展开,法理学研究中重要的学术争论主要体现在对法学基本概念的争论(如有关权利本位的争论)上。
本书处理的主题属于法理学研究中的传统问题,与学界已有的研究相比,本书力图在以下几个方面形成自身的特点:
其一,普遍性。这里所谓的普遍性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我所谓的法学基本概念并不是限定于某个特定法域的独特概念系统,它既不限于中国,也不限于外国;既不限于大陆法系,也不限于英美法系。如果尚不能主张这套概念系统像逻辑规则那样完全超越了任何时空限制的话,那么它至少应被视为可以在整个现代法律制度和学术共同体中加以普遍适用。当然毋庸置疑的是,当代中国的法律制度实践和学术话语是本书所隐含的语境,当代中国法理学对法学基本概念的权威界定在许多时候也构成了本书研究的出发点和检讨对象。在许多情况下,我对特定法学基本概念的厘定体现了我对中国学界相关讨论的关注和呼应。
另一方面,所谓普遍性还涉及法学基本概念和部门法学研究之间的关系。法学基本概念不是对已有部门法学概念的简单拔高或归纳,以至于在此部门法中或许通行,在彼部门法中则无法被认可。例如,如果主要基于民法教义学的考虑定义“法律行为”这个概念,则很难获得民法学之外的认可。法学基本概念也不是法理学生造出来的、与部门法学无直接关联的空中楼阁,以至于部门法学的研究者可以简单地说,这是法理学中的××概念,我们对××概念的理解与之无关。我希望本书所厘定的各个概念能与部门法中的相关概念产生联系,它们一旦被认为是正确的,则必定可以有效适用至部门法学中,哪怕它们看上去与现有部门法中的相关概念有所抵牾。例如,如果本书所界定的法律行为概念是正确的,那么它一定反映了民法学者使用法律行为概念原本所要表达的意义,哪怕其表达方式看上去与之有所不同。总之,在普遍性的意义上,本书所厘定的法学基本概念可以被看成某种超时空或超部门法学的“法学总论”或“一般法学说”的组成部分。
其二,科学主义。在一本谈论概念的著作中强调科学或许有些古怪——尽管这里的科学并非那种狭隘的经验科学或形式科学。我使用“科学”所要强调的是,本书会尽量避免在讨论法学基本概念时采取强的规范主义立场或形而上学立场——这两种立场均是非科学的(并非贬义的)。就规范主义而言, 人们有时会认为证成(justify)而非说明(explain)某个概念才是概念研究的正确立场。我将在第三章有关法律规范概念的讨论中详细阐述这种区分。这里只需要强调的是, 本书致力于为各类法学基本概念给出一个定义,而不去关注该概念所涉及的正当性问题。例如,本书力图为法律领域的“权力”概念给出合理的定义,非常关注当人们主张某甲享有法律权力时,他们实际上是什么意思。但这里必然存在某些证成问题,法律赋予某甲权力而没有赋予某乙权力, 这是需要某些实质(道德)理由的,而这些实质理由则不在本书的研究范围之内。不仅如此,某些规范主义者还会主张说,某个概念并没有什么专门的意涵,概念只是人们达到某个规范目标或实现某种价值的工具,只要有利于这些目标或价值,人们可以为概念赋予他们所希望的任何内容。例如,如果将法律行为定义为X而不是Y,可以更好地实现交易安全,那么法律行为的定义就是X。这样一来,概念理论实际上将成为某种法伦理学或法政策学的一部分。在一般情况下,本书均不致力于某种实质的规范理论,也不认为某种实质的规范立场会影响到本书对某个特定概念的理解——尽管可以说,许多法学基本概念本身就是“关于”某种规范立场的概念。我的看法毋宁是,法理学需要首先确认概念的定义问题,再去借此解决相关的实质理由问题。当然,本书有时会接受某种弱的规范主义,这是说,某种非实质的、有利于认知的价值立场,的确是我进行概念厘定时的考量因素。例如,如果将法律行为定义为X而不是Y,可以更好地理解或认识法律地位的产生方式,那么便有了将法律行为定义为X的理由,这个理由属于规范意义上的理由,但它不是某种实质的规范立场。
所谓形而上学立场是说,对概念的厘定包含着对事物“本质”的界定。例如,如果想对“权力”作出正确的界定,那么这个过程一定包含了对权力本质的发现。在界定法学基本概念时,人们所面对的是人类长期以来形成的法律实践和话语惯习,许多概念明显是被这些实践和惯习所构造出来的“人工语言”。我并不认为这里存在什么特殊的本质或古怪的实体决定了某个概念必须被如何使用;也没有什么“自然如此”“原本如此”的世界本原要求我们必须如此使用某个概念。对规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对,使得本书的概念分析陷入某种(非典型的)语义学方法中,我将在第二章专门处理这个问题。
其三,弱化考据。本书是较为理论化的基础性研究,许多法学基本概念的历史渊源可能早在古罗马法中就已发端,近代以来又被诸多知名学人反复阐发。对此,某种比较常见而妥当的研究方法是一头扎入学术史的故纸堆中,确认这些概念最初含义,系统地梳理这些概念在学术史中的演变,再以此为基础提出自己的观点。本书并不会采取这种方法。在我看来,弄清楚某位作者究竟说了什么以及他为什么这么说,与确认某个概念的理论工作是两件不同性质的事情,前者即便可以为后者提供某种基础和准备,也不能替代后者。多数法学基本概念在现当代的法律话语中已经具备了初步的共识,重点应当是将这种共识加以澄清或精确化,分析这些概念的工作原理,而不是学术考古似的确认这种共识的来源或流变。或者说,重要的是经典作者们的意见是否正确,而不是他说了什么或他为什么这么说。在这个过程中,呈现学术史的完整性并非本书追求的目标,一些或许也为某个概念提供过重要洞见的作者会被忽略。然而,弱化考据完全不等于不倚重学术史。事实上,对于处理这样抽象的议题来说,不倚重学术史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负责的。在很多情况下,某种在学者间已经形成的通说概念,是我们目前继续沿用该通说的理由(但也不是唯一的理由),这往往是本书研究的起点,尽管完全没有异议的通说其实并不常见。在更多的情况下,本书宁愿将学术史作为自己对话的对象,通过对相关作者理论的检讨和批评,展示我本人对特定概念的厘定。事实上,对于本书来说最重要的对话作者限于如下几位:霍菲尔德、凯尔森、拉兹、塞尔(John Searle),以及以张文显教授为代表的当代中国法理学权威作者。
最后,本书的书名包含“导论”字样,这并不是一种谦虚。我强调的意思是,本书恰恰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产物。尽管我在本书中提出了许多不同意见,但在上述巨人思想面前,我并不认为自己的观点有明显的“独创性”。在很大程度上,这本书依然没有走出某种“读书心得”的范畴。就此,本书仍旧是我思考这类问题的一个中继点(如果说不是起点的话)。同时,我也希望本书的问世能够让更多的学人学子了解到相关议题的真实存在与研究价值,进而推动对这些议题更为深入的研究。
马驰,甘肃天水人,法学博士,天津商业大学法学院教授,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访问学者(2017年)。主要研究领域为法理论与法哲学。在《法制与社会发展》《中国法律评论》《环球法律评论》《华东政法大学学报》等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多篇,主持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多项。
法学基本概念相关理论是各类法学研究的概念工具和法理学教学的重要内容,同时可能为其他部门法学提供理论支持。本书便是对权利、义务、法律主体、法律规范、法律渊源、法律行为等法学基本概念的专门研究,处理的主题属于法理学研究中的传统问题。与学界已有的研究相比,本书的研究具有普遍性、科学主义、弱化考据等特点。传统的法学概念体系有过于简单粗糙之嫌,作者希望借此研究让更多的学人学子了解到相关议题的真实存在与研究价值,进而推动对这些议题更为深入的研究。
导言
第一章 法理学、分析法理学与概念分析
一、法理学的范围
二、分析法理学与概念分析
第二章 法学基本概念的性质
一、法学基本概念的意义
二、法学基本概念的功用
三、法学基本概念的依据
第三章 法律规范
一、导言
二、理性主义与意志论
三、句法学、语义学与语用学
四、句法论与语义论
五、语用论
第四章 法律规范的效力
一、两个讨论前提
二、三种观点与两个维度
三、法律约束力说与法律资格说
四、法律效力的概念:约束力说与资格说的统一
五、法律效力判断句的性质
六、从法律规范效力的概念到法律规范的概念
第五章 法律规范与法律的结构
一、法律的结构问题的基本含义
二、法律规范个别化理论
三、法律规范的类型理论
四、法律规范的要素理论
第六章 法律渊源
一、有关法律渊源概念的三个疑难
二、从法律本体论到法律认识论
三、法律规范、法律渊源及其认识论层级
四、非正式法律渊源
五、作为操作性理由的法律渊源
第七章 再论法律渊源
一、典型法律渊源概念的意义
二、法律渊源的识别标准
三、非法律渊源(类型D)
四、外部法源(类型C)
五、非权威的法律理由(类型B)
第八章 法律地位概述
一、法律地位的基本类型
二、法律地位的独特性
三、法律地位与法律规范
第九章 法律义务
一、义务的规范意义
二、义务与制裁
三、义务性规范与制裁
第十章 法律许可
一、许可是否具有规范性
二、反射命题与相互定义命题
三、强许可与弱许可
四、作为规范命题的强许可与规范语用论
五、排他性许可
第十一章 法律权力
一、权力的范围
二、权力改变法律地位的方式
三、权力的构成性
四、授权性规范的还原
第十二章 法律权利
一、权利的语义分析
二、权利义务的对应问题
三、权利的保护对象
四、权利的规范意义
第十三章 法律责任
一、责任的歧义
二、作为后果的责任概念
三、作为应遭的责任概念
四、法律责任与法律权力
第十四章 法律主体
一、法律主体概念的理论分歧
二、基于不同类型权利义务的内部实在论
三、拟制主体与人工智能的法律主体问题
第十五章 法律行为
一、两种法律行为概念
二、不限于表意行为的法律行为概念
三、限于表意行为的普遍法律行为概念
四、作为宣告式言语行为的法律行为
五、民事法律行为的特殊性
六、其他涉法行为
参考文献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