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编辑推荐
经典作品,备受推荐,中国史学习者和爱好者的必读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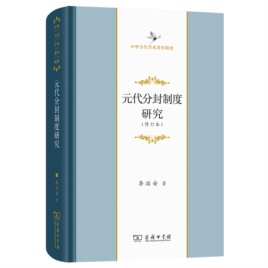
定价:¥198.00
经典作品,备受推荐,中国史学习者和爱好者的必读作品
元代分封制并没有像唐、宋、金分封那样名存实亡,而是一种较完善的贵族权力、爵位、财产分配制度。它植根于蒙古草原家产分配和黄金氏族共权传统,较大范围地封土封民。封君在部分领地内临民治政,且以领属占有人户为重心。在大蒙古国军事扩张和政治体制趋于皇帝集权的过程中,分封制度得以逐步演化,从而包容了兀鲁思分封、五户丝食邑、私属分拨、宗王出镇四种不同形态和有关王府衙门、爵位等级等方面的一系列规则。来自蒙古草原分封传统的元代分封制度,不能不受蒙元统治方式部分汉化总趋势的影响。元代分封制中相当多的具体内容,实际上是草原传统与汉地制度相互渗透、结合的产物。而且,随着元朝廷中央集权的逐步加强,分封制度本身也出现了草原因素下降、汉法因素上升的变动。当然,这只是和蒙古原有的东西作比较。如果从汉族王朝相关制度的发展进程看,元代分封及其引起的贵族封君在中央、地方的较大权势,又似为对唐宋皇权官僚政治强化、分封制衰微历史趋势的一种逆转。本书通过对元代分封制度进行的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尽可能地从不同侧面和角度展现了元代分封制度的全部面貌,资料丰富,立论严谨,见解独到,对了解和研究元朝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大有裨益。
增订本面世18年之后,承蒙商务印书馆收入“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而再版,深感欣慰!这个修订本没有增补新的论文,只是修订若干文字,增添了少量的相关史料。对某些古籍版本,也做了必要的调整。希望尽可能提供一个较为满意的文本,以飨读者同仁。
需要申明,有关贵戚驸马所都千户及领地的资料颇显不足。尤其是漠北斡亦剌部、宁昌路亦乞列思部的文字记载几乎寥若晨星。因此,笔者以上论述多以弘吉剌部资料为主,似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阐明投下组织的两大类型,是认真研究分封制及军制的必要前提。基于此,就可以正确地分辨史籍中“五投下”“十投下”“十七投下”的属性了。据笔者拙见,《元史·兵志二·宿卫》中的“五投下探马赤”和《金史·国用安传》中的“十七头项”,是军队投下。《通制条格》卷2至元八年圣旨中的“纳陈驸马、帖里干驸马、头辇哥国王、锻真、忽都虎五投下户计”,《元史· 孛鲁传》《齐荣显传》中的“十投下”,则统属分封投下。《黑鞑事略》中的十七头项,则以军队投下为主。其中皇子皇弟投下又兼有分封投下之义。就是说,即使是同一字样的“五投下”“十七投下”等,在不同场合也可分别指谓军队投下或分封投下。如果把它们混淆起来,就容易引出不应有的误解。
附带说明一下投下分封与忽必(qubi)、莎余儿合勒(soyurgal)分封的关系。村上正二从蒙古语忽必、莎余儿合勒二词的分析入手,认为成吉思汗把家产分配原则融入家族分封,各男性氏族成员均有权占有草原千户部民的忽必分子而组成兀鲁思。其他贵戚、功臣只能享受莎余儿合勒(恩赐),不得染指忽必分子。这是很正确的。但是,村上正二进而把忽必分封与草原部民固定在一起,以为由掳掠人户组成的诸王私属不属于忽必,而属于莎余儿合勒(恩赐)。这就未免失于拘泥和武断了。《元朝秘史》说,朮赤、察合台、窝阔台三兄弟征服兀笼格赤城,“将百姓分了,不曾留下太祖处的分子”。此处的“分”与“分子”,蒙古语汉字音写即为“忽必牙勒都周”和“忽必”。就是说,蒙古人把军前掳掠百姓在皇室中的分配,也称为“忽必”。此类掳掠百姓当为皇帝和诸王的私属民,而非草原千户民。这不难说明,忽必分封当是宗王分封的总原则。它施用于草原兀鲁思分封,也施用于宗王私属分拨和食邑分封。或者可以说,宗王分封投下均属忽必分封范围。与此相对,莎余儿合勒分封应是贵戚功臣分封的总原则。它施用于贵戚功臣的私属分拨和食邑分封。或者可以说,贵戚功臣分封投下都属于莎余儿合勒分封范围。
京ICP备05007371号|京ICP证15083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1884号 版权所有 2004 商务印书馆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1884号 版权所有 2004 商务印书馆
地址: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邮编:100710|E-mail: bainianziyuan@cp.com.cn
产品隐私权声明 本公司法律顾问: 大成律师事务所曾波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