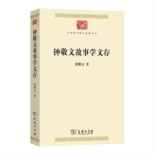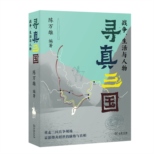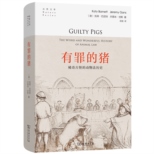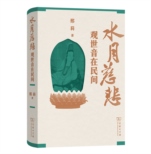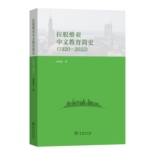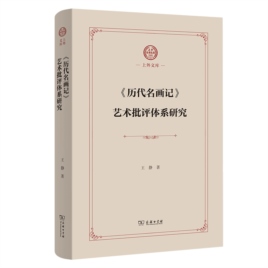“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有唐一代的文艺巨匠们在诗、文、书、画各领域创造了空前的繁荣景象,魏晋南北朝时期对于艺术形式与美学理论的探索,在唐王朝那种意气风发、雄强自信、多元交融、兼收并蓄的社会环境和思想氛围中,缔结出为后世称道的臻于完美的艺术成果。这个艺术实践的“黄金时代”往往被认为是“没有理论的时代”。从理论深度来看,对于人格的自由与解放、宇宙生命玄远的追求以及美的本体探问,的确难以超脱魏晋时期富有哲学精神的探究与思考;从理论内容来看,魏晋时期那些标志着时人审美意识自觉的理论范畴,如“形神”“意象”“神思”“风骨”“气韵”“滋味”等,基本奠定了后世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的发展方向。这些说法具有一定的现实性,但忽视了唐代艺术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现象,那就是艺术批评的价值意义。可以说,作为文艺盛唐气象的余音或回响,唐代的鉴赏家们通过自身的妙悟与传达,对于艺术创造巅峰时期的作品和现象进行观照、体悟、品评、反思,并将深刻而丰富的审美经验进行提升与凝练,形成了如盛唐后殷璠“兴象”说,王昌龄“三境”说,皎然“境界”说,刘禹锡“境生象外”说等。故而,基于拓展和创新意义上的艺术理论构建,唐代或许不是后世标举的典范,但如果从审美鉴识的角度切入,盛唐艺术的繁盛为美感经验的探索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创作于中晚唐时期的画学著作《历代名画记》,历来被认为内容广博、理论精深、结构完备,其绘画品评及铨量诸家优劣的部分蕴含着丰富的理论内涵,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和深入清理,因此,从艺术批评的视角对《历代名画记》进行考察,对于深入民族特有的审美心理结构,理解其背后的文化传统和哲学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