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联图书
-
燕云在望:“永久黄”西迁往事1937—1952¥85.00
尚有大星一颗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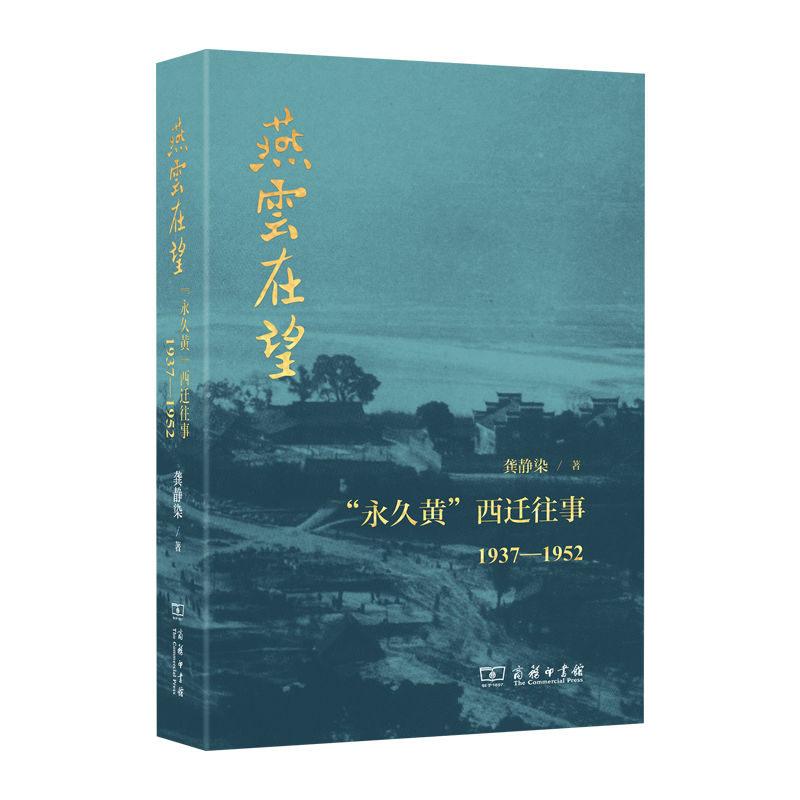
《燕云在望:“永久黄”西迁往事1937—1952》(商务印书馆2024年出版)
南京江北新区大厂街道宁六公路东侧,有一座纪念广场。广场正中矗立一尊铜像,他就是被毛泽东誉为“工业先导、功在中华”的“中国民族化学工业之父”范旭东。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范旭东和他的同道先后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精盐工厂久大盐厂、中国第一家制碱厂永利碱厂、中国第一个私营化工研究机构黄海化工研究社(合称“永久黄”团体)。而他整整90年前在南京创办的永利硫酸铵厂(即永利铔厂),不仅是中国第一家制酸厂,而且是当时亚洲最大的化肥生产企业,中国的第一袋化肥,第一包催化剂,第一套合成氨、硫酸和硝酸化工装置等,都从这里诞生。
然而,“永久黄”团体的开创性事业,绝非一路鲜花着锦凯歌行进,相反,他们筚路蓝缕命途多舛,特别是在抗战的硝烟中,“永久黄”的千百同仁拼尽全力与战争赛跑,以常人无法想象的坚忍与毅力,勉力保存下这“吾国惟一化学命脉”。作家龚静染积20年之力,以极大的耐心搜集史料,遍访旧人,完成了《燕云在望》一书,首次生动而翔实地记录“永久黄”身陷家国困厄,却倾力奋斗、微光成炬的西迁往事。
兴办硫酸铵厂,是现代中国的一件大事,硫酸铵不仅是现代化肥的主要原料,也是军火原料硝酸的主要来源,“平和时代为农田肥料之泉源,一旦国有缓急则改造军火以效力于疆场”,其重要性足以左右国家兴衰。九一八事变后,范旭东调查发现,日本已建立13家化工厂,每年生产的合成氨超过70万吨,中国的耕地面积是日本的30倍,却没有一家化工厂!他疾呼“深盼于国家存亡呼吸之顷,毅然以全力促成(硫酸铵厂的创办),为中国存万祀千秋之命脉”。在他的奔走努力下,1935年9月18日,永利铔厂办公楼在南京六合落成,工厂正式入驻办公。这一天,与会来宾坐船从下关出发,经八卦洲到卸甲甸厂区,遥望新厂房“雄踞江岸,气象之新,令人心壮”。范旭东特意选在这一天举办开工典礼,就是为了不忘国耻,“今日九一八,吾辈在此摄影,伫候东北四省光复时,再共摄一影”。1937年2月5日,中国人自己生产的第一桶硫酸铵出炉,范旭东在公函中难掩兴奋:“列强争雄之合成铔高压工业,在中华于焉实现矣。”
一切都是新的,就像一颗种子种下去,然后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这是承平年代最普通的际遇,也是1937年春天永利铔厂的缩影。然而这个春天太短暂了。仅仅半年之后,七七事变爆发,淞沪会战旋即打响,永利步入沦陷的前夜。
1937年8月21日清晨,6架敌机飞临厂区上空,掷下5枚炸弹。身在外地的范旭东立刻给工厂发去电报:“吾辈当以最大忍耐与信心,克服一切困难,为祖国化工尽瘁至敌人屈服而后已,幸毋悲愤,仍当努力恢复工作。”随着战事逼近,11月中旬以后,与学校、机关一样,一幅史无前例的工厂企业流亡图卷惊心动魄地展开了。
由安徽而湖北,再到重庆,“永久黄”的西迁历程,只是这幅壮阔画卷中的一角。1938年3月,“永久黄”全部员工迁渝;9月,久大自贡模范制盐厂开业;1941年,重庆永利碱厂初步落成;同年,侯氏制碱法研制成功;1942年,中国最深之井开凿成功,发现天然气和黑卤……如此大规模的企业集团在物资匮乏、交通拥塞的西南腹地诞生,在历史上是罕见的,既是苦难,也是壮举。幸赖龚静染先生的丰富史料和一支健笔,我们得以感受到无数历史细节背后的悲壮底色和家国情怀。
范旭东、侯德榜、孙学悟等“永久黄”的领袖和骨干,是宏阔眼光、胸怀和抱负的大商人、大学人,他们的名山事业同时展现了近代中国启蒙与救国的双重变奏。即使在抗战最艰难的境况下也绝不将就,用范旭东的话说,“情肯不做,做就做好,做就做成……否则势必永久呻吟于落后的不利地位”。
1942年12月12日,九龙半岛沦陷。第二天一早,《大公报》编辑徐铸成去看望避居香港的范旭东。这位60岁的老人一夜无眠,看上去精神却很好。他对徐铸成说,“我昨晚听了一夜炮声,很高兴。了解到日军炸弹的爆炸力很有限,可见它的炸药制造并不怎么先进,我们再努力一把,完全有可能追过它”。他接着说:“我们在化学工业方面力求进步,产品在国际上列入先进的行列,那就在这方面立了一根坚实的柱子。中国有这样几十根柱子,基础就牢了。有了这些柱子,终有一天,会盖好一幢举世瞩目的堂皇大厦。”徐铸成说他听了以后肃然起敬,竟至泪下。
三年以后,范旭东抱憾辞世。追悼会上,一个女工送来挽词:“我们工人永远不会忘记你”。周恩来、王若飞合署的挽联上写着:“遗恨渤海留残业,深痛中国失先生”。
(原载于啊《现代快报》2024年11月17日B05版)
- 语文课要解决“想”的问题2024-11-27
- 寻找改变饮食生活的根源2024-11-22
- 昆廷•斯金纳“语境主义”探究2024-11-22
- 思想的邮差2024-11-16
- 经济战争是终极的风险博弈2024-11-15
京ICP备05007371号|京ICP证15083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1884号 版权所有 2004 商务印书馆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1884号 版权所有 2004 商务印书馆
地址: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邮编:100710|E-mail: bainianziyuan@cp.com.cn
产品隐私权声明 本公司法律顾问: 大成律师事务所曾波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