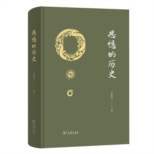关联图书
-
思想的历史¥0.00
观念使思想具有历史——《思想的历史》读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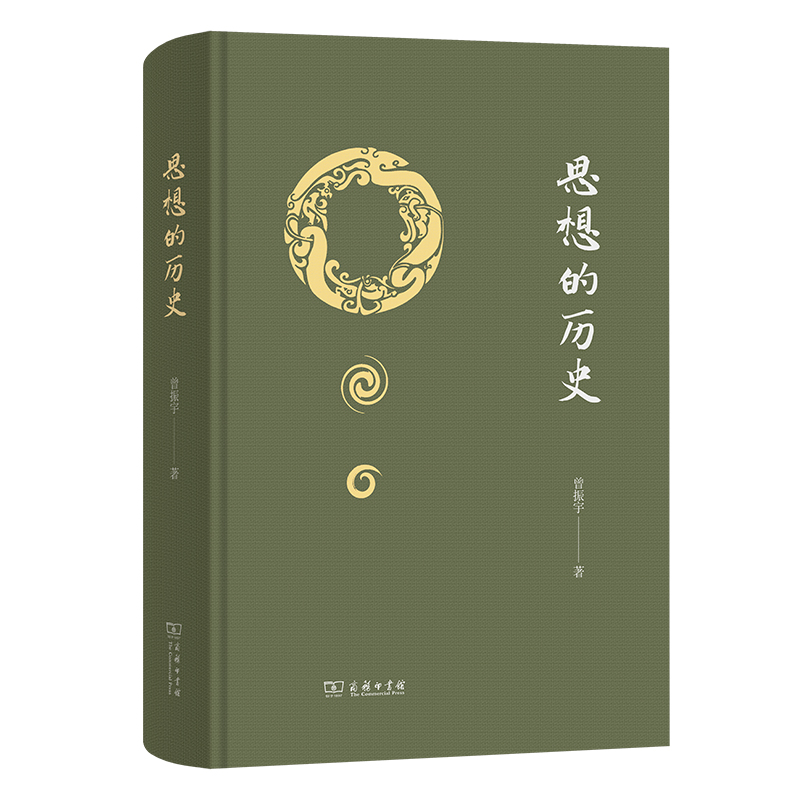
《思想的历史》(商务印书馆2025年出版)
近代学者柳诒徵先生曾提出,“充满宇宙皆历史”“一切文字皆历史”(柳诒徵《史学概论·史学之范围》)。细思其说,“充满宇宙”者,不只是有形可见的物质,还有绵延不绝的思想。物质可灭,思想却可改头换面,重组再生,并以一种合乎时代的样貌左右时代。至于“文字”,也不只是作为一种记载过去的工具,以媒介之身专供后来的史学家查阅。在更深层的意义上,文字的使用及书写者对于某种东西的呈现,也折射着书写者自身对于世界的理解。长此以往,文字也就具有了某种思想史的价值。曾振宇教授《思想的历史》(商务印书馆2025年5月出版)一书,便与思想的历史化问题密切相关。该著汇集了作者20余年来对儒、墨、道、法等学派之核心问题的思考,其中不乏独到见解。
观念史研究兴起于20世纪初的美国。但长期以来,中国学者并未热衷此道。近些年来方偶有倡导此学并作出示范者。曾振宇教授曾在多个场合提倡从观念史角度对中国历史上的哲学流派、哲学体系开展研究,并关注某一时代集体思想中的结晶体,指出在人类政治、经济、文化和道德观的变迁中,深刻影响人类生活方式、价值观和历史进程的,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有社会文化形态的观念。
《思想的历史》所探究的与其说是某种思想的客观历史,不如说某种思想被历史上某些人的不同理解以及产生的不同效应。这正是观念史研究要着力呈现的内容。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说:“真正的历史思考必须同时想到它自己的历史性。只有这样,它才不会去追逐某个历史对象的幽灵,而是学会在对象中认出自身的他在性并因而认识自己和他者。”思想家、哲学家首先不是创造思想的人,更非复制某种思想的人,而是不断地重新理解历史上某种思想的人。只有如此,思想才会构成历史。雅思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不妨从以上角度来理解。具体到中国思想史,“仁”“义”“礼”“智”“信”“孝”“性”“情”“天下”“道”“无为”“逍遥”“自然”等思想,业已在先秦时期概念化、范畴化。在此基础上,两汉以来的思想家,其学说大致沿两种路向而生:
第一,继续思考先秦哲人留下的问题,于旧学说中再度提取、阐释某个范畴。比如在思考人伦与治理天下的问题时,董仲舒在宽严、指向两个维度上提出“以仁安人,以义正我”(《春秋繁露·仁义法》)。他对“义”的理解,与先秦时期以“宜”释“义”和以“正”释“义”皆有不同。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既其来有自,又构成了董氏的教化新说。在中国古代的涉外理念及天下观念中,皆可寻见以上踪影。
第二,通过厘定诸概念之间的关系,确立某种作为社会规范的价值体系。最典型者如魏晋思想家对于“名教”“自然”之关系的讨论,以及对于“性”“情”之表里、主次关系的阐述。这些思考被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人在何种程度上是自由的”所统摄。
以上两种路向时有交叉。但无论如何,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概念的出现和人们对某种概念的阐述,以及对不同概念之间关系的厘定,均标志着人们对支配自身的某种观念展开反思,也标志着观念从一个对人而言的支配性角色转向被支配的角色,人们有了塑造某种在其看来正确观念的动机。虽然概念范畴会在一定程度上破坏思想的生动性、原发性,但那些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哲学家,通常是对某种思想理解较深并以概念范畴凝练其理解的人。他们期待这些概念范畴成为一种具有规范性的理念。
循以上思路,兹举《思想的历史》对儒家之“仁”与老庄之“道”的论述,并加入笔者的一己之思,以期呈现出该书在思想史、观念史研究中的若干侧面。
第一,释原发之“仁”。作者根据孔子及其弟子语录,指出“仁”具有不可言说性。这种不可言说性,不是指“仁”神秘莫测,与日常生活龃龉隔膜,而是在于,“仁”可以通达人生、日常的各个方面,使人一言难以说尽。这也表明,“仁”不可被概念化,不可作为一种抽象的道德原则被说者灌输,被听者套用。职是之故,孔子论“仁”,多从具体生活情境中引发问者之实感、深思。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说,孔子只是一个讲“常识道德”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离开思辨,并不说明一个人的思想便流于肤浅。孔子对“仁”的非思辨式论述,构造的是一种超乎形上—形下对立的原发构成式境域。这种境域通过“能近取譬”,指点“为仁之方”,使不同的问“仁”者获得对于“仁”的直接把握,而非知识、概念上的知晓。因此,作者说:“知性认识无法达到对本体的概念性把握,……孔子之‘仁’,在本体论上是一种可能的知识,而不是现实的知识。”这种“可能”,不仅包括“仁”具有各种面向,还包括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发动自我而成为仁者——“吾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仁的公共性,以及每个人成为仁者的可能性,不仅表明“人性平等,在孔子思想中已有萌芽”,而且意味着人人具有成为新的自我的自由。至陆象山号召与天下人“共进乎仁”,仁义在思想世界就被提升至“人的自然权利”的高度。陆氏的号召,“可以说是自由思想的儒家式表达”。
第二,辨老庄之“道”。司马迁曾谓庄子之学“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后人习惯于并称“老庄”,多少受太史公之说影响。《思想的历史》所侧重的是,老庄“思想体系在内在旨趣与特点等方面的差异性”。作者指出,“《老子》道论有多重义项,道既是超验的、无限的,又是‘物’‘象’‘精’”,庄子之“道”则“无时间与空间特性,无始终与聚散过程……道虽无具体规定性,却具有无限的遍在性。”《老子》之“道”常常被对象化地阐述。王弼批评老子说“无”而言必及“有”,“恒言无所不足”(《三国志·魏志》卷二八《钟会传》,裴松之注引何劭《王弼传》),所针对的正是老子说“道”而导致“道”的具体化。这种具体化,亦可谓“‘物’属性”。至于庄子之“道”的“无限的遍在性”,应与太史公所说的“其学无所不窥”(《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有关。
但老庄之“道”并非迥然相异,而是有某种共同的朝向,并合力构成了一种有别于西方符合论真理观的中国真理观。这种真理观的基本特点在于,对通过语言、文字、教化凝固起来的外在标准持反思、批判的态度,强调人对于某种合乎人性的本真状态的自然呈现。西方侧重通过“为学”而掌握真理,中国则强调通过“为道”而彰显真理。《老子》以“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老子·四十八章》)确立中国哲学真理观的主基调,庄子则通过“以道观之”(《庄子·秋水》),把逍遥自由作为“人生的最高目标与幸福之所在”。如果说西方真理观强调“做加法”,那么道家发明的中国真理观,更倾向于“做减法”。这种“做减法”的真理观,非仅停留于思维方式的层面,而且隐然构筑了道家的政治理想和自由观。作者指出,《老子》文本中的“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是一种体现“忘”的精神,人相适于大道的逍遥境界。作者以《庄子》中的逍遥境界解释《老子》中的理想社会,与王叔之(穆夜)对“逍遥”的解释暗相契合,表明自由的根据在内而不在外。这种自由,便是“积极自由”。
与自然科学不同,涉及人文方面的研究常常带着地域、国度的前缀。这是因为,人们坚信文化具有多样性。由此,通过外来学说重新理解本土文化、“牺牲本土哲学的独创性以换取所谓现代性与科学性”的“反向格义”现象不断被反思。比如,《思想的历史》一书在讨论老子哲学时,就谨慎地避免用现成的西方哲学概念定义“道”;在考察严复与中国古代气学的西化时,说“每一种哲学与文化形态中的概念,因为自身赋有的独创性而呈现出‘不可译性’”。所以,严复据西学逻辑标准而重构的中国之“气”,“让国人既感到熟悉又陌生”。
但作者也指出,在某个时代,人类毕竟具有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比如,“在人类文明‘轴心时代’,宇宙万物生成与运动、变化的动力因问题曾经是困扰着整个世界文明的一大哲学难题。”所以中西比较的眼光也必不可少。由于观念是体现文化差异的典型要素,观念史研究就需要考察人类对同一个问题、同一种现象的多种思考和据之开展的多种活动。而观念的绵延与变迁,总是通过对古今中西问题的不断思考来实现。至此,是否可以说,观念不仅使思想具有历史,而且使这种历史保持着一种面向全人类的、比较的、批判的性格?
(原载于《中华读书报》2025年08月06日15版,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文化传播学院助理研究员)
- 作为样本的蒙塔尤:权力统辖、文化认同与历史意识2025-07-18
- “获而一无所获”与人生的意义2025-07-16
- 八十万言丈量思想——舟山籍学人许明龙重译《论法的精神》纪事2025-04-25
- 思想的邮差2024-11-16
- 古树轮写大历史2024-09-04
京ICP备05007371号|京ICP证15083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1884号 版权所有 2004 商务印书馆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1884号 版权所有 2004 商务印书馆
地址: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邮编:100710|E-mail: bainianziyuan@cp.com.cn
产品隐私权声明 本公司法律顾问: 大成律师事务所曾波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