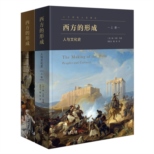关联图书
-
西方的形成:人与文化史¥458.00
《西方的形成》:一部光荣与荆棘交织的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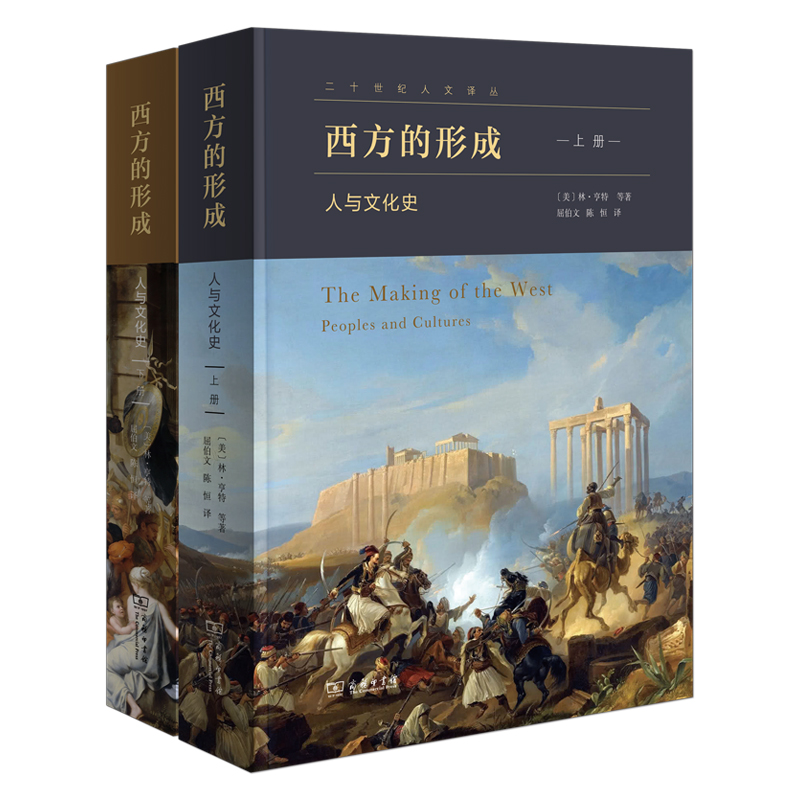
《西方的形成:人与文化史》(商务印书馆2025年出版)
当提及“西方”时,人们往往联想到雅典卫城的白色廊柱、罗马斗兽场的沧桑石墙、启蒙运动的理性辩论或工业革命的机器轰鸣。这种固化的意象将西方塑造成一个自古以来就边界清晰、特质恒定的“文明标杆”。然而,林·亨特等史家合著的《西方的形成:人与文化史》通过三千年的历史细节,更新了人们的这种认知。这部兼具学术深度与大众可读性的著作,既展现了西方创造民主制度、科学突破和艺术繁荣的“光荣”面,也毫不避讳地揭露了其殖民掠夺、奴隶制和内部冲突的“荆棘”史。它不是西方优越论的赞歌,而是通过解构文明神话,让我们在复杂的历史纹理中理解:西方并非天生优越的特殊存在,而是多元文明互动的产物;现代世界的面貌,正源于这种光荣与荆棘交织的演变过程。
一、叙事革命:从“孤立进化”到“全球共生”
传统西方史观犹如一座坚固的堡垒,常常将古希腊奉为文明的“绝对源头”,后续的发展就像沿着这条预设好的“主线”线性延续。在这种史观的叙事里,西方文明仿佛是天生的宠儿,从诞生之初就沿着一条独特且优越的道路不断前进,其他文明不过是这条道路的陪衬。然而,本书明确指出,西方文明并非是孤立发展起来的,而是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东地中海及希腊人群相互交往的产物。这就好比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是由多个不同的画师共同绘制而成,每个画师都贡献了自己独特的色彩和笔触。希腊人最初就像好奇的探索者,通过近东邻居接触到了天文学、数学等知识。这些知识就像一把把钥匙,为希腊人打开了一扇通往更广阔知识世界的大门。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更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促成了希腊与近东文明的深度融合,希腊化时代政治、社会和文化的交汇,就像是一场盛大的宴会,各种思想、文化和制度在这里碰撞、融合,为罗马及后世西方奠定了基础。牛津大学教授约瑟芬·奎因(Josephine Quinn)在《世界如何塑造了西方》(How the World Made the West)中进一步证明,将西方文明简化为希腊—罗马叙事是19世纪殖民主义的产物。她追溯西方文明的根源至巴比伦法典、腓尼基航海术、阿拉伯学术乃至游牧民族的冶金技术,证明每一次文明跃升都依赖外部输入。例如,希腊字母源自腓尼基;罗马法律吸收了希腊哲学;中世纪经院哲学融合了阿拉伯学术。
本书变革了传统叙事中将非西方文明视为背景板的视角。当欧洲陷入中世纪“黑暗时代”时,阿拉伯文艺复兴(8—13世纪)就像是一盏明灯,保存并发展了古希腊、罗马文化。阿拔斯王朝建立的智慧宫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他们在这里共同探讨学问,推动代数、医学和天文学的突破。花拉子密的代数学著作直接影响了欧洲数学发展,就像是一颗石子投入了欧洲数学的湖泊,激起了层层涟漪。技术传播更深刻改变了西方文明进程:中国造纸术经阿拉伯传入后,使知识传播成本骤降,马丁·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迅速传遍欧洲,就是纸张带来的便利的最好例证;指南针为航海家指明了方向,助力达·伽马绕过好望角,推动了地理大发现;火药瓦解了封建城堡,加速民族国家形成,打破了封建制度的枷锁。
与此同时,本书并未回避全球互动残酷的一面。哥伦布航行开启的大西洋三角贸易,导致千万以上非洲人被贩卖至美洲(1850年前)。奴隶船上的恶劣条件(剃发烙印、男女分离、四分之一死亡率)和种植园的残酷剥削(每日15—17小时劳动),为欧洲工业革命的原始积累助力。美洲原住民则遭受家园的丧失,以及疾病和战争所带来的死亡,其文化被污名化为“野蛮”,从而给掠夺行为披上一层合法外衣。经济史家彭慕兰的“大分流”理论在此得到印证:18世纪前欧亚发展水平相当,西方的领先源于美洲白银、非洲奴隶及对亚洲资源的掠夺,而非内在优越性。本书揭示了西方的“光荣”始终与被掠夺者的血泪紧密相连。
二、内在裂痕:西方文明的自我博弈
西方标榜的“自由”始终伴随着压迫。古希腊民主仅限成年男性公民(雅典25万居民中奴隶占10万以上),女性和被征服者被完全排除在外。启蒙运动提倡的“自由、平等、博爱”与殖民奴役并行:伏尔泰拥有黑奴,洛克投资奴隶贸易,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宣扬平等却蓄奴百人。
科学革命常被视为“理性战胜信仰”,但本书展示了两者的持久纠缠。哥白尼临终前才出版《天体运行论》,伽利略被迫公开放弃日心说,牛顿毕生研究炼金术和神学。更吊诡的是,猎巫(15—18世纪处决数万所谓的“女巫”)恰发生在科学革命时期——弱势群体被妖魔化为替罪羊,表明理性并未完全取代迷信。
书中指出,“西方”作为一个“统一实体”的形象,更多是冷战时期地缘政治的产物,而非历史常态。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陷入长期分裂(法兰克帝国昙花一现、神圣罗马帝国内部邦国林立等)。宗教改革引发三十年战争(1618—1648),天主教与新教的冲突强化了民族国家意识。20世纪更上演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但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就像是一把双刃剑,在带来破坏的同时,也带来机遇,比如催生技术创新(如两次世界大战催生了计算机、核能),意识形态分歧激发社会改革(如福利国家的建立)。
三、未竟的解构与对二元对立的超越
尽管在许多方面有所突破,本书在若干方面仍难逃“西方惯性”,表现在:1.西方中心论残余。在本书叙事中,非西方文明多被呈现为影响的给予者或接受者,作为西方文明发展的背景或辅助力量出现,其自身的发展脉络和内在逻辑(如中国明清的经济创新、伊斯兰世界的科学传统)很少得到深入探讨。2.进步史观幽灵。“走向现代西方”的目的论是一个隐含的预设,读者在阅读中似乎被暗示,所有文明都在朝现代西方的方向发展,这就忽视了非西方文明自身的发展路径和选择。3.精英视角主导。政治史聚焦国王、贵族,文化史围绕学者、艺术家,女性、劳工、少数族裔(如犹太人、吉普赛人)的贡献,虽有零星提及,却未能有机地融入叙事主线,更多时候成了主流叙事的点缀。
阅读《西方的形成》,我们既看到了西方文明的“光荣”——它在多元互动中创造了民主、科学、艺术的辉煌,为现代世界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也看到了它的“荆棘”——它在殖民扩张中犯下的暴力罪行,在内部矛盾中经历的撕裂痛苦。它让我们认识到:西方不是一个固定的、完美的“文明模板”,而是一个在光荣与荆棘中不断演进的“流动过程”;它的形成,是人类文明共同参与的结果,既包含了创造与进步,也包含了毁灭与倒退。
理解西方,本质上是理解现代世界的由来——我们今日所处的全球政治体系、经济秩序、文化思潮,都深深打上了西方的烙印。但更重要的是,理解西方也是理解我们自身——西方的故事是一面镜子,它所展现的光明与黑暗、理想与现实的落差,是所有文明都在面对的普遍性问题。
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交织的今天,《西方的形成》给予我们的最大启示,是超越二元对立,拒绝将“西方”与“非西方”视为“优越”与“落后”的对立,而是将其视为人类文明的不同样态。希腊吸收了埃及的智慧,罗马借鉴了希腊的文化,阿拉伯保存了罗马的学术,西方又从阿拉伯与东方吸收了技术。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动,才是文明发展的常态。
读懂《西方的形成》,最终是为了以更审慎、更富同理心的姿态,面对人类共同的未来,既尊重不同文明的独特性,也承认人类经验的共通性;既警惕任何形式的“文明优越论”,也不陷入“文明孤立论”的误区。就像作者在前言中指出的那样,西方的历史是一个“仍在展开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处在完结状态的结果”,而在世界文明的长河中,我们都是“形成中”的参与者,而非“完成态”的评判者。
(原载于《中华读书报》2025年10月8日10版,作者为上海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 观念使思想具有历史——《思想的历史》读后2025-08-06
- 作为样本的蒙塔尤:权力统辖、文化认同与历史意识2025-07-18
- “获而一无所获”与人生的意义2025-07-16
- 一个世纪的轮回——巴恩斯史学与中国的西方史学译介2024-12-09
- 古树轮写大历史2024-09-04
京ICP备05007371号|京ICP证15083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1884号 版权所有 2004 商务印书馆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1884号 版权所有 2004 商务印书馆
地址: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邮编:100710|E-mail: bainianziyuan@cp.com.cn
产品隐私权声明 本公司法律顾问: 大成律师事务所曾波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