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编辑推荐
丝绸之路、欧亚草原游牧民族历史及文化爱好者、研究者丝绸之路、欧亚草原游牧民族历史及文化爱好者、研究者
10—11 世纪发生在欧亚大陆上的一次规模宏大的民族迁徙10—11 世纪发生在欧亚大陆上的一次规模宏大的民族迁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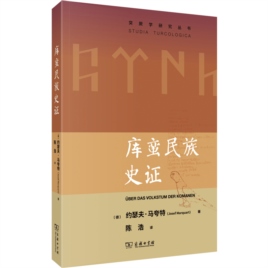
定价:¥62.00
丝绸之路、欧亚草原游牧民族历史及文化爱好者、研究者丝绸之路、欧亚草原游牧民族历史及文化爱好者、研究者
10—11 世纪发生在欧亚大陆上的一次规模宏大的民族迁徙10—11 世纪发生在欧亚大陆上的一次规模宏大的民族迁徙
本书属于“突厥学研究丛书”第四种。作者约瑟夫•马夸特(Josef Marquart)在《库蛮民族史证》一书中利用汉文、波斯文、阿拉伯文、古代突厥文、希腊文、拉丁文、俄文等多种语言的史料,勾勒了10—11世纪之际发生在欧亚大陆上的一次规模宏大的民族迁徙。作者把欧亚大陆西部的库蛮或波罗维茨与欧亚大陆东部的靺鞨、奚等民族联系起来,并对不同史料记载进行条分缕析和去伪存真,显示出作者精湛的史学素养和对重大历史课题的驾驭能力。本书在西方学界享有盛誉,此番首次译成中文,相信一定会推进中国学术界的相关研究。
今天我们该如何阅读一部100年前的欧洲东方学著作?
约瑟夫·马夸特( Josef Marquart/Markwart),德国著名的东方学家,专长伊朗学和突厥学,治学兴趣集中于欧亚大陆的历史地理学。马夸特于 1864年12月9日出生于德国莱亨巴赫( Reichenbach)的一个农家,早年在图宾根大学学习天主教神学,后来转读古典语文学和历史学。获博士学位后,他前往荷兰莱顿工作。 1912年,马夸特受聘为柏林大学的伊朗语和亚美尼亚语的全职教授,此后一直在柏林教书,直至1930年2月4日去世。马夸特无疑是德国东方学谱系中一颗璀璨的星,他不仅在伊朗学领域内著作等身,甚至在突厥学,尤其是对突厥碑铭的纪年问题,也做出过划时代的贡献。
马夸特在《库蛮民族史证》一书中利用多语种史料,勾勒了公元10—11世纪发生在欧亚大陆上的一次规模宏大的民族迁徙。马夸特在书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中世纪穆斯林文献中的“昆”(即库蛮),甚至包括“凯伊”(即奥斯曼人传说中的先祖),可能源自中国东北的民族 —靺鞨。后来在历史上出现的“钦察”,则是源自与契丹关系密切的奚。钦察西迁的历史背景,是辽、金的改朝换代之际。他们与马札尔人、库蛮人和哈喇契丹人一起前往里海以北地区,其中哈喇契丹人前往基马克和昆人的地盘。作者认为广义上的“钦察”,其主体人口是乌古斯人,但吸收了昆人(库蛮)并采纳了他们的族名。于是,在某个历史阶段,汉文史料中的“钦察”,与俄文史料中的“波罗维茨”( Половьци,单数形式 Половець),以及拉丁文史料中的“库蛮”( Koman/Coman)和阿拉伯语文献中的“昆”( Qūn),指的其实是同一个人群。
马夸特精通多种东西方语言,在书中从阿拉伯语、波斯语、亚美尼亚语、叙利亚语、俄语文献中摘译了大量史料,例如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七世的《帝国行政论》,叙利亚主教米海尔的编年史,还有亚美尼亚史家乌玛窦,以及穆斯林史家诸如亚库特、穆罕默德·奥菲、伊本·阿西尔、加尔迪兹和拉施特等。此书译成汉文后,也为我们中国从事西北民族史的学者,提供了大量一手史料,且其中多数语言是我们不太熟悉的。尤为重要的是,马夸特还结合域外文献,对汉文史料中(例如《北史·勿吉传》《元史·土土哈传》和《元史·速不台传》)出现的地名、人名和族名进行了详尽的考订。所以,《库蛮民族史证》这部书的汉译,对于我国北方民族史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马夸特的这部书于 1901年1月动笔, 7月完成初稿,只是第 1—3节。初稿提交之后,作者又补写了第4—8节,以及附录部分。全书直到1914年7月才出版,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本书写作的过程中,还爆发了两次巴尔干战争。作者没有脱离社会现实,在文中经常借题发挥,同情保加利亚人,鞭挞奥斯曼人 —即便这种态度与当时德国的官方立场相左。马夸特用“刽子手”“嗜血的野兽”等露骨字眼来形容奥斯曼苏丹哈米德二世,称他是与苏拉、尼禄、曼苏尔、皮萨罗和罗伯斯庇尔齐名的暴虐之君,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恶劣和城府最深的卑鄙之徒。
在奥斯曼帝国内部,Turk是一个极具贬抑色彩的称谓,指代“愚昧和野蛮的”安纳托利亚底层农民,而奥斯曼统治精英的自我认同是“奥斯曼人”。但是马夸特认为,恰恰相反,现实中的奥斯曼人反复无常、诡计多端、拐弯抹角和毫无底线,辅之以妄自尊大和无节制地越权。真正意义上的“突厥人”则是具有优等品质的民族,例如伏尔加河流域的不里阿耳人。马夸特指出,奥斯曼人把小亚细亚、亚美尼亚、东南欧和叙利亚的文明,淹没在血腥、犯罪和暴力所汇成的汪洋大海中长达六个多世纪。在马夸特的眼中,整个巴尔干半岛,从莱塔河和德拉瓦河,只有保加利亚人才是唯一诚实的民族 —突厥语人群的直率和尚武的品性,与斯拉夫式的忍耐和对农事的热衷,在保加利亚人身上有幸得到了融合。他反对德国与奥斯曼帝国结盟对付保加利亚,并认为作为基督徒的保加利亚人应该是西欧的天然盟友。
马夸特对奥斯曼人的偏见和对保加利亚人的同情,源于他认为基督教文明要比伊斯兰教文明更加优越,是欧洲中心论的表现。爱德华·萨义德把浸润在东方学学术土壤中的欧洲优越感,批判得体无完肤,并重重地扣上了一顶“东方主义”的帽子。在萨义德写作《东方学》的 1970年代,有同情巴勒斯坦人的政治和道德动力,但这种动力在当下已经式微了。被奉为后现代史学开山鼻祖的萨义德,似乎没有耐心去梳理东方学三百年的实证主义学术传统,更缺乏客观和专业的评论。
东方学从17世纪起逐渐发展成为一门专门的学术领域,19世纪达到巅峰,二战以后影响力开始消退。在当下的学术体系中,东方学内部的各个分支渐次独立,或与区域研究,或与史学研究合流,更加符合当下人才培养的目标。东方学诞生于启蒙时代,其学术理路是揭示隐藏于事物背后的、不为人知的联系(Zusammenhang),以此创造出新的“知识”。这种以“联系”为核心的知识生产,或是把史料中两个不同名称的人物比定为同一个人,或是把不同时空内的民族或人群通过迁徙和起源叙事搭建起共同的纽带。法国东方学家德金在18世纪中叶就尝试过把匈奴与匈人、柔然与阿瓦尔人、突厥与土耳其人联系起来。他的这些假设,直到今天仍然是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课题。马夸特的这部书,则把中国东北的靺鞨与西方的库蛮联系了起来。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德国汉学家夏德曾在《跋暾欲谷碑》中硬生生地把阿史德元珍和暾欲谷“揭示”为同一个历史人物,其实也是遵循了自启蒙时代以来的这条东方学思想脉络。
东方学所强调的具有启蒙色彩的“联系”,与近几十年来流行的全球史有异曲同工之处。全球史也强调“联系”。当代著名的全球史家于尔根·奥斯特哈默指出,全球史就是世界性体系内的互动史,处于其核心位置的不仅是全球性联系,也有在全球性结构条件下的联系。他在一次访谈中,对自我的定位就是一个“老派的启蒙主义辩护者”。康拉德也曾言简意赅地指出,全球史就是把历史进程、事件和人物,放置于全球互联的语境中考察。
我们该如何对待欧洲东方学的学术积累?中国有自身的史学传统,不能简单地用“落后多少年”这样的标准去衡量与西方学术的差距。人文学术的研究,更注重的是学者个体的修炼。如果我们在学术训练阶段,掌握足够多的工具语言,积极学习新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就可以站到学术的前沿。在尽可能掌握东方学研究成果的前提下,做到继往开来 —既要对传统的“语文学”方法有所坚守,也要以诸如“全球史”的新学术范式来审视传统的学术议题,甚至开拓崭新的领域,方能推动学术的进步。
京ICP备05007371号|京ICP证15083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1884号 版权所有 2004 商务印书馆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1884号 版权所有 2004 商务印书馆
地址: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邮编:100710|E-mail: bainianziyuan@cp.com.cn
产品隐私权声明 本公司法律顾问: 大成律师事务所曾波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