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编辑推荐
首部从非西方视角全面考察国际关系思想的开拓之作
本书在《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构建》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和梳理印度、中国和伊斯兰世界三大文明体系中有关国际关系或世界秩序的思想和实践,把非西方的历史经验纳入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体系的开拓性探索,是西方学术界第一本系统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视角讨论三大文明体系中国际关系思想及其来源的学术专著,具有开拓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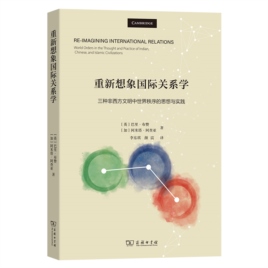
定价:¥39.00
首部从非西方视角全面考察国际关系思想的开拓之作
本书在《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构建》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和梳理印度、中国和伊斯兰世界三大文明体系中有关国际关系或世界秩序的思想和实践,把非西方的历史经验纳入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体系的开拓性探索,是西方学术界第一本系统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视角讨论三大文明体系中国际关系思想及其来源的学术专著,具有开拓意义。
国际关系学传统上是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视角为主导的。然而,基于对国际关系自身起源与两个多世纪以来国际关系实践与理论历史的反思,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巴里·布赞和阿米塔·阿查亚对传统国际关系学提出了挑战,主张把非西方的历史经验和思想遗产纳入国际关系学理论研究,构建起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全球国际关系学”。两位作者在书中通过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包括古代印度、中国和伊斯兰世界在内的三种非西方文明有关世界秩序的思考与实践,“重新想象”了国际关系学或可呈现的三种不同面貌,极大地丰富了国际关系理论思想史,为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深入研究奠定了更为深厚的基础。
19世纪前叶以降,以西方大国为主,再加上俄罗斯和日本在内的少数国家,一直主宰着世界政治,这是没有争议的(Buzan and Lawson,2015)。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现代国际关系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段经历所塑造的,这一点也没有争议(Acharya and Buzan,2019)。该学科的大部分思想都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从所有重要的方面来看,西方历史或多或少就是世界历史。这是胜利者的叙事和思维方式,也是我们对由此产生的欧洲中心主义进行有力指控的基础。我们严肃对待这一指控有两个原因。第一,在国际关系学领域还存在一些被西方主导地位所否定的其他故事和思维方式。如果我们要建立一个更为全球性的国际关系学,或曰“全球国际关系学”,这些故事不可或缺。第二,西方主导的时期现在已经结束,胜利者的国际关系学叙事的结构不仅在外围,而且在中心都在削弱。那些有着其他故事的地方正重新成为财富、权力和文化权威的中心。与此同时,它们将自己的故事、概念和思维方式带入当代国际关系学的实践和思想中。因此,这些曾被边缘化的故事和理解方式得以重新植入当代世界秩序,中国、印度和伊斯兰世界则占据了突出的位置。
本书的目的是通过对印度、中国和伊斯兰世界的国际关系/世界秩序的思想与实践进行考察,揭示那些被边缘化的故事。这个目标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它考察如果国际关系学理论是在西方以外的文明中发展起来的,将会是什么样子的。这不仅是对历史的一次异乎寻常的,或者说趣味性的冒险尝试。正如我们在较早的作品中详细论述的那样(Buzan,2011;Acharya,2014;Buzan and Lawson,2015;Acharya and Buzan,2019),尝试这样做的主要原因在于,这一问题不仅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实践有深刻的影响,对致力于围绕国际问题进行思考和理论化的国际关系学亦是如此。第二,它打开了重新思考现代国际关系学历史、概念和理论之门。这些之前被边缘化的故事和思维方式,是与现代国际关系学有很多共同点,还是在基本方面对它提出了挑战?概念是否是共享的?如果是的话,它们是否具有相同的含义;或者,反映不同历史的替代物是否会破坏现有的“剧目”?
根据我们的理解,国际体系/社会现在正迅速形成一个深度多元主义的结构,即前外围/殖民地世界的相当一部分正在以自己的方式成功地获得现代性,它们不仅在财富和权力方面,而且也在对文化和政治权威的支配中赶超着西方。在很多地方,新的财富、权力和复兴的文化权威已足够显著,以至于给西方带来了军事、经济、法律、社会和政治方面的难题。此外,它们还与一种依旧强烈的后殖民心结有着广泛的联系:要理解这一点,只需要注意到中国依旧对此十分重视,不仅是为了铭记它的“百年屈辱”,还要使之渗入日常外交和国内政策中。相比之下,虽然西方舆论对其国内和历史中的种族主义依然敏感,但基本上忘记或边缘化了帝国时代西方对其他民族实施的种族歧视与压迫,尽管其中的白人民族主义者正在使与当代移民有关的种族主义重新合法化。近40年前,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1984)曾担心第三世界“对西方的造反”。而这种造反仍将可能被忽视,且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过,因为这种造反背后的新近去殖民化的国家和人民,大多是贫穷的、弱小的和文化上被削弱的。西方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于向第三世界提供对外援助的承诺,期待它们轻松且自动地沿着自由主义的道路发展。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实际上意味着西方化(Spruyt,2020:344—346)。现在,前外围地区的相当一部分正在变得强大,并在叩击中心地区的大门。它们正在寻找,或者在某些情况下,如中国、韩国和新加坡,已经找到了它们自己的现代化之路,且不是对西方的克隆,而是其传统文化与现代性的独特融合。它们对西方和日本的历史积怨不能再被搁置一边。
在西方主导的时代,主要是由欧洲白人国家,再加上日本构成的少数第一批现代化国家主导,它们根据自身的利益和偏好塑造了国际体系/社会。而这个时代显然行将全面结束。一种全新的国际结构正在形成,在这种结构中,共享现代性的均质化效应与日益扩大的文化、政治分化共存。资本主义而非自由民主赢得了冷战,现在那些国家在某种意义上都是资本主义的。这一结果使1989年以前的那种世界秩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这种共享的资本主义分化为从民主到专制的多种政治形式(Buzan and Lawson,2014),反映了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从等级制到平等主义的不同文化。由此产生的辩证法根植于西方创造的高度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世界之中。新兴的深度多元主义世界秩序不仅是由现代性的传播和深化所推动的,而且现代性的展开正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共同命运问题,从气候变化和疾病控制,到大规模灭绝和污染,再到经济管理、网络安全和恐怖主义。
全球国际体系/社会向深度多元主义的转变对国际关系学科提出了深刻的挑战。正如我们在最近的一本书(Acharya and Buzan,2019)中提出的,过去两个世纪,现代国际关系学思想一直相当密切地追随着国际关系的实践。坦率地说,正如后殖民学者经常指出的那样,这导致国际关系学成为一门高度以欧洲为中心的学科。旨在研究整个人类的学科,其视角竟如此狭隘,这不仅是个明显的讽刺,也是亟待解决的本质性问题。
这一情况形成的原因是清晰的。现代国际关系学科是在过去两个世纪中形成的,恰好与西方文明成为主导文明并将之强加给其他文明的时间相吻合。在此期间,这种强加的行为产生了覆盖性效应,让一种文明史无前例地成为全球性霸权。现代国际关系学正是在西方凌驾于其他所有文明之上时发展起来的,这使之不可避免地成为一门欧洲中心主义的学科。从19世纪中期直到21世纪初,我们可以说,西方史,尤其是由盎格鲁圈(Anglosphere)所主导的解释现代性的政治经济学,在很多重要方面已经成为世界史和全球政治经济学。
——摘自本书导论,注释从略
京ICP备05007371号|京ICP证15083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1884号 版权所有 2004 商务印书馆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1884号 版权所有 2004 商务印书馆
地址: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邮编:100710|E-mail: bainianziyuan@cp.com.cn
产品隐私权声明 本公司法律顾问: 大成律师事务所曾波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