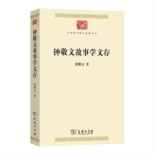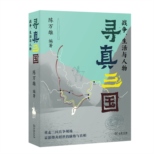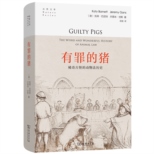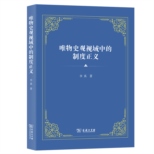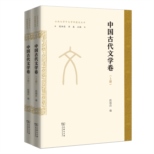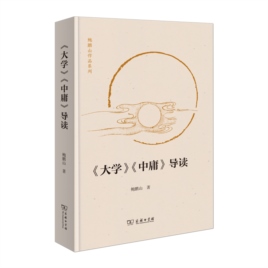《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儒家经典“四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和民族文化信仰的儒学,唐以前,以“五经”为经典,《论语》和《孟子》并未正式列为“经”,《大学》和《中庸》也只是《礼记》中的两篇,没有获得独立的、特殊的地位。“四书”概念之正式确立归功于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是其标志。其中,《大学》《中庸》中的注释解析称为“章句”,《论语》《孟子》中的注释解读因为采集了历代一些学者的说法,称为“集注”,后人合称其为“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
朱熹把这四本书合为一体而注释之,是因为朱熹认为《大学》中“经”的部分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的部分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而由子思“笔之于书,以授孟子”。既然这四本书分别与圣人(孔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子)有关而自成“圣学”体系,一以贯之,理当合为一体。
“四书”包含了儒家对宇宙、社会、政治以至个人道德生活的整体理解和主张,是中国人精神世界和信仰世界的总阐述,所以朱熹说:“若理会得此‘四书’,何书不可读,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处!”朱熹之后,中国教育和学术重“四书”胜过“五经”,科举考试以“四书”为主要科目,“四书”遂成为中国文化传承文明延续的主要载体。
《大学》《中庸》这两篇厕身《礼记》的文章被推崇而终至于单列,有其自身的逻辑。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就推崇《大学》与《中庸》,陈寅恪《论韩愈》曰:
盖天竺佛教传入中国时,而吾国文化史已达甚高之程度,故必须改造,以蕲适合吾民族、政治、社会传统之特性,六朝僧徒“格义”之学(详见拙著《支愍度学说考》),即是此种努力之表现,儒家书中具有系统易被利用者,则为《小戴记》之《中庸》,梁武帝已作尝试矣。(《隋书三二经籍志》经部有梁武帝撰《中庸讲疏》一卷,又《私记制旨中庸义》五卷。)然《中庸》一篇虽可利用,以沟通儒释心性抽象之差异,而于政治社会具体上华夏天竺两种学说之冲突,尚不能求得一调和贯彻,自成体系之论点。退之首先发见《小戴记》中《大学》一篇,阐明其说,抽象之心性与具体之政治社会组织可以融会无碍,即尽量谈心说性,兼能济世安民,虽相反而实相成,天竺为体,华夏为用,退之于此以奠定后来宋代新儒学之基础。退之固是不世出之人杰,若不受新禅宗之影响,恐亦不克臻至此。
陈寅恪正确地指出了韩愈(字退之)道统之说及其对《大学》《中庸》的独具只眼的推崇,都是一方面为了抗衡佛教思想,一方面又由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起意建立了儒家之道(统)。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仅儒家道统的建立动机上出于佛教的刺激、方法上模仿袭用佛教的经籍传习和统绪传承,即使《大学》《中庸》这两篇文章受到重视乃至最后单独成书而有“四书”之目,其实也是因应佛教的挑战而作的应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