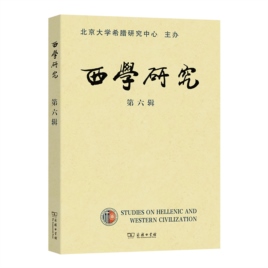现代希腊之外,对于发生在希腊这个地理单元上的人类历史,在成为人们认知与研究的对象时,大多都会被切割成不同历史时期,分属不同的学科与研究领域。古希腊历史是西方古典学的基石,中古时段的历史大致可以归属于拜占庭帝国史。一般而言,这两段古代历史在国际学界并没有明确的民族属性,但奥斯曼帝国统治以来的历史尤其是1821年希腊独立战争以来的历史往往会被视为现代希腊国家的历史。然而希腊国家之外这种对希腊这片土地上过往历史的“割裂”并不融于现代希腊人的自我认知,自19世纪中叶希腊民族主义史学兴起直到现在,希腊官方史学以及由此所塑造的大多数普通希腊人的历史意识中,希腊民族的历史从古至今从未中断,是统一而连续的民族历史。希腊民族主义史学的奠基人帕帕里科普罗斯(Constantinos Paparrigopoulos,1815—1891)于19世纪中后期相继完成的鸿篇巨制《希腊民族史》(Ιστορία του Ελληνικού Έθνους,15卷,1860—1875)从神话时代写到希腊1821年独立战争;进入20世纪,希腊举全国之力,联合众学者编写了全新的同名希腊历史《希腊民族史》(17卷),从石器时代写到1974年希腊推翻军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加入欧共体等一系列重要的当代历史事件。时间来到21世纪,希腊人对于统一民族历史的求索与坚持丝毫没有松动,这方面的代表作也是一部集众人之力完成的《希腊历史》(Ελληνική Ιστορία,2007),时间跨度与前一本众人之作吻合,只是篇幅略有缩减,更适合普通读者。
但希腊人之外,写作古今一统的希腊历史的尝试并不常见。尽管《爱丁堡希腊人历史》( The Edinburgh History of the Greeks)系列可以算作这方面的突破,但这套成于众手的丛书至今仍止步于拜占庭及之后的希腊人历史,尚未兑现丛书策划者所承诺的从古至今的3500年历史。因此,英国学者比顿的新作《希腊3500年》(Roderick Beaton,The Greeks,A Global History)确实是这方面难得一见的完整作品。然而比顿与希腊民族史著作的共同点怕也只能局限于所书写的历史时间长度相仿,正如该书的英文标题所示,比顿试图书写的是一部希腊人的“全球史”,探讨的是希腊人的全球性影响。全球史的视角本身就是对民族主义视野的颠覆,这也决定了比顿的这部希腊历史并非为构建统一的现代希腊民族而著。而且比顿书中对于希腊人的定义也不同于希腊的民族史学,比顿认为的希腊人是所有“说希腊语的人”,这看似单一的标准事实上给出了希腊人最宽泛之定义,这不仅意味着语言之外的诸如地域、血缘这类的物理、生物标准可被排除在希腊人认同要素之外,也意味着凡认同希腊语所承载之文化者都可被视为希腊人,而这种希腊语传承的文化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历史长河中经历了漫长曲折的流转变化,这就是比顿所承诺的,他讲述的是这样的希腊人的“多种身份认同故事”。事实上,比顿对希腊人多重身份认同的揭示就是为了挑战一种长期存在的“单向度的、彼此互斥的认同”,他的书与其说对何为希腊人提供一个标准答案,不如说是在探究关乎希腊人身份认同演进的复杂多变的历史过程。而这种过程优先的考察思路也恰与民族主义史学以一种先入为主的预设为出发点,然后寻求历史证据的知识生成过程背道而驰,并与后者形成鲜明对照,进而为熟悉希腊民族主义史学范式的读者提供了一种跳脱藩篱、重审历史的可能。
——摘自《西学研究》第六辑,第279—2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