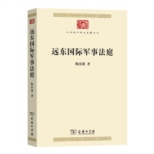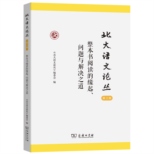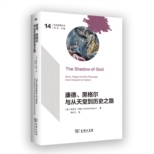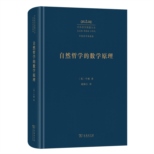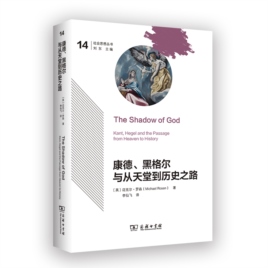显示全部编辑推荐
哈佛大学教授重磅新作,首次揭示现代理性社会背后的神学思维。思想史类图书的典范之作,专业论证与清晰文笔的完美结合,兼具学术深度与阅读愉悦,不容错过的思想探险!
相关推荐:
迈克尔·罗森凭借其渊博学识以及精度分析和批判性想象力的独特结合,为我们提供了一场辩证法盛宴:他通过展示这些世俗主义思想家如何沉浸在现存的宗教思想形式中,使德国理想主义重获新生。这部杰作是阿多诺曾称之为“在形而上学衰落之际”与之团结的一个佳例。
——莱纳·福斯特,法兰克福大学教授
关于英语世界伦理思维的性质和有效性的讨论,[现有]案例范围太窄了。……迈克尔·罗森重新审视了康德的传统,并开辟了更广泛的关键问题。他的书写得清晰而引人入胜,可以活跃和改变眼前这场辩论。它需要被广泛阅读。
——查尔斯·泰勒,麦吉尔大学教授
迈克尔·罗森重新讲述了从康德到黑格尔的故事,将其核心描述为“从天堂到历史之路”。这是一本引人入胜的书,文笔优美,论证严密,充满见解和智慧。
——埃克卡特·福斯特,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
★视野广阔,欧洲思想史的壮阔画卷尽收眼底
本书是一本浓缩18—19世纪欧洲思想精华的读物。作者诠释康德、黑格尔哲学著作的同时,时时向哲学史溯源寻根,屡屡环顾左右求证,苏格拉底、柏拉图、赫尔德、席勒、谢林、费希特、斯宾诺莎、卢梭,也都参与这场思想史会饮中,在读者眼前展开一幅跨越千百年的思想长卷。
★新颖独到,揭示神学阴影下的现代性悖论
本书的视角挑战常识,极具思想冲击力,激发了我们对现代性自身前提的批判性思考。作者犀利指出塑造现代社会的根本问题:当信仰不再是公共道德和政治秩序的绝对基石后,我们为何必须遵守道德规范?这不仅仅是历史洞见,更是深刻的现代性批判。
★洞见深邃,直击康德、黑格尔理性主义哲学的核心
读过本书,读者可以瞬间把握康德、黑格尔乃至当代许多哲学辩论的深层关注和问题核心。无论是对康德、黑格尔哲学,还是对一般伦理学思考感兴趣,本书作为一个很好的入门起点,定能深化读者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现代社会规范性基础之脆弱性、保守性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