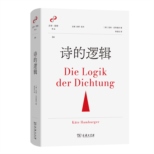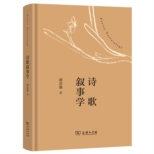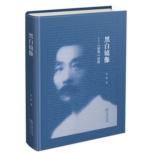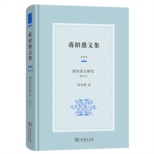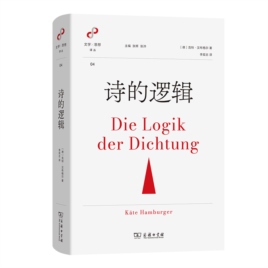章节一:
诗的逻辑并不顾及发挥描述与表达功能的语言,因而也不考虑这样一个多少显得平庸的事实:文学作为语词艺术就是语言的艺术。诗的逻辑更多是出自这一状况,即语言作为文学的构型材料,同时也是让特殊的人类生活得以完成自身的媒介。这并不是新的认识。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August Wilhelm Schlegel)就曾经表述过这一点,他说的是“诗的媒介也正是人类精神赖以抵达沉思,控制住自己随意勾连蔓延的想象的同一个媒介:语言”。这句话也暗示,这一媒介不是仅仅由载入意义的符号,也即由词汇组成,它还以深刻得多的方式确定了以特殊的艺术本质而存在的文学。诗的逻辑或语言逻辑因而并不意味着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语言批判,而是可以更准确地称之为语言理论,该理论研究的是,造就文学形式的语言(我们暂且这么泛泛地说)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从功能上与我们在生活中进行思考和转述的语言区别开来。作为文学的语言理论,诗的逻辑是以文学与普遍语言体系的关系为对象的。诗的逻辑因而要在语言理论的意义上来理解,而这里所指的语言理论在下文中将作为起点理论得以展开,在阐述过程中能以其自身取代逻辑这个术语。
关于文学的形形色色的新旧理论在我看来都没有达到完全令人满意的结果,因为文学与普遍语言体系的关系并没有就其本身得到足够敏锐的把握,或者我们始终没有从中推出最后的结论。唯有进行了这项工作之后,独具特色的、文学自身所特有的现象才会显现出来,即文学是一个难以界定的艺术领域,甚至是“那种艺术在其身上开始自行消解的特殊艺术”,正如黑格尔所看到的;我们也会立刻看到,黑格尔的这一洞见的缘由出自何处,还有哪些他自己当然没有推出的结论可以从中推演而出。因为如果严肃对待这一见识,它的方法论价值就会展示出来。它会照进文学中暗藏的逻辑织网,文学正是通过这一织网与普遍的思维及语言过程的织网既相连又分离。但是在揭示这一结构时也会有特殊的、往往令人惊诧的现象暴露出来。尤其昭然可见的是,诗学的核心难题,也即文类难题,会在另一个角度下,在另一种秩序原则下得到展示,有别于迄今我们所熟悉的角度和原则,不论后者是否已经而且仍将继续变幻多样。歌德从古典诗学中挣脱出来,将抒情诗、史诗(Epik)和戏剧描述为独有的三个“自然形式”[ 在《西东合集》(West-östliche Divan)之注解与论文中 ],但完全没有将它们绑定于传统文类,而是认为它们“在最小的诗中往往也会”一同发挥作用。自此以后,新近的诗学中尤其吸纳了这一观点。埃米尔·施泰格(Emil Staiger)就推出了新的文学阐释可能,他从传统的形式概念中提炼出了抒情性、史诗性和戏剧性,将之视为灵魂基本倾向的凝固:记忆、想象和张力。在他之前,罗伯特·哈特尔(Robert Hartl)就将文类归结为体验形式,“心绪的能力”:感受力、认知力和欲求力。
章节二:
从语言理论上来论证史诗类(叙事类)文学和戏剧类文学作为虚构文学之前,应该首先就文学虚构(literarische Fiktion)的概念做一番讨论。因为被用于极其不同现象的“虚构”(名词)和“虚构的”(形容词)概念在文学研究中通常也是在或多或少并不准确的意义上,比如凭空生造的意义上来理解的。而且英语中所用的fiction,被用来指称长篇小说(以替代较为旧式的novel),但是不用来指称戏剧,这种用法加剧了这个概念及其用法的不准确性。由此更有必要将其定义为一个准确的文学研究方法概念,将其与平时那些意义和用法区分开来。
虚构是从拉丁语 fingere 衍生出来的,后者包含了极为不同的意义,如描画、杜撰及欺骗性的编造。我们只要检验动词 fingere的意义和活着的西欧语言中由它衍生出的名词和形容词,对于什么——尤其在与接下来要发展出的文学理论的关联中——应当被理解为文学虚构,我们就会得到一个近乎准确的定义。fingere 在意大利语中是 fingere,在法语中是 feindre,在英语中是 to feign,在德语中是 fingieren,这意味着,这个拉丁语动词在现代语言形式中仅仅保留了这一意义:伪造,假冒,装作等。与其相应的名词 Finta、feinte、feint、Finte 也是在此基础上添加而成的。但是名词 fictio 就不一样了。这个词在活着的语言中虽然还保留了fingere 的贬义或者改良义,但是后者,也即对创造性构型的功能的指涉压过了其贬义。至少在法语里,随后在德语里,形容词fictif(fiktiv)在 feint, fingiert 之外,是在积极的意义内涵上建立起来的,这种内涵在艺术理论中比名词 Fiktion 本身还更常见。
这样一来,情形也变得复杂了。fingiert和fiktiv之间的区别意味着什么,我们说到一部小说或戏剧中的人物不说他们是捏造出来的,而说是虚构的,这个事实意味着什么呢?这和艺术中的想象构成物又有什么关系呢?“虚构”的名词(Fiktion)和形容词(fiktiv)作为概念在多大程度上是确切的,对什么来说是确切的?自从汉斯·费英格(Hans Vaihinger)的《仿佛哲学》(1911年)面世以来,人们习惯于以仿佛如此(Als-Ob)的形式,也即通过伪造状态的结构来解释虚构。这对于科学——数学、物理学、法学等——的虚构是确切的。数学计算的是无空间的点,物理学计算的是空的空间,就仿佛真的存在这样的空间,法学考察的是构造出的案例,就仿佛它们是真实发生的一样。将虚构定义成仿佛如此的结构,使用的是非真实的虚拟式(irrelais),也必须使用它,这个虚拟式表明了自己的伪造状态。在语言使用中,伪造和虚构概念的确接近。数学上的点是伪造的,也是虚构的构成物。在日常语言中,虚构的形容词和名词都具有非真实的、捏造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