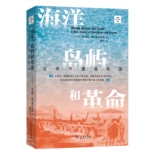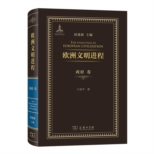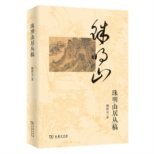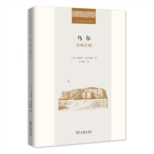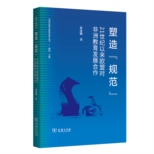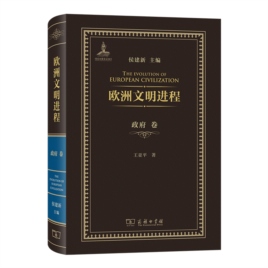余论
在西欧近代历史中,无论是法国的绝对主义王权,还是英国的专制君主制,抑或德意志的邦君专制,都强调立法在政治统治中的职能,但是立法权掌握在专制的君主手中,法国的三级会议、英国的等级议会和德意志的邦君等级会议都是如此。也正是因为如此,17世纪晚期以及进入18世纪以后,各国议会通过和颁布的法令都有所减少,这似乎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君主制发展到了鼎盛时期,“随之而来的是混乱无序的暴政、无所适从的集权和中央集权的无政府状态”;因此,对“旧制度”的批判不绝于耳,要求进行改革,提出了各种政体的模式,在18世纪的欧洲政治思想领域中出现了一个活跃的、贴上了“启蒙运动”标签的学术大争论,政治学的、哲学的、宗教学的、经济学的以及社会学的和历史学的学者们都加入其中,“引发了一系列围绕着各种重大问题的学说之争,形成了那一时期知识分子、政论家甚至一些国家首脑的‘百年战争’”。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政治理论家马克·戈尔迪和罗伯特·沃克勒主编的集合了英美和欧洲其他国家数十位享誉学界的知名教授撰写的《剑桥十八世纪政治思想史》对这个“百年战争”进行了全面而详细的阐释,列举了一系列活跃在这个世纪的、对学界来说耳熟能详的政论家的名字: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休谟、康德、费希特以及亚当·斯密等。著述者们批评性地评判了先哲们的思想及其产生的历史影响,把这个世纪的思想论争看作“现代性来临的标志”。这个世纪的思想家们都受过系统的大学教育,有着极为雄厚的知识学养,他们中间相当一部分人还有着参与执政的丰富实践,所以能够把知识和权力有机结合起来,提出的政治理念和思想或能对已经发生过的英国革命进行理论注解,或对远离欧洲的美洲大陆产生重大的影响,或是为法国大革命的发生提供了思想动力。
启蒙运动时代被誉为“理性的时代”,它发端于英国,这与“光荣革命”的发生不无关系。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以有限的君主制取代了绝对君主制,君主政体虽然保留下来,但是其权力受到支配议会的内阁成员的控制,议会成为主权者。在18世纪,国王、上议院和下议院的组建具有了现代政府的三种职能:“国王是行政部门的首领,上议院是最高的司法机构,下议院是主要的立法机构。”英国的政治实践与政治传统理论发生了严重的冲突。自中世纪以来,欧洲政治理论的核心是“君权神授”,宗教改革以及在各国先后实行的君主专制制度都对这一神学政治理论产生了极大的冲击,英国发生的“光荣革命”更是在政治实践中否定了“君权神授”。美国学者帕特里克·赖利就认为:“新教的个人道德自律观念很自然地从神学与道德哲学延伸到政治学,由此形成了社会契约论的理论基础。”英国哲学家洛克于1689年出版的《政府论》填补了“君权神授”理论崩溃之后留下的真空。在《政府论》中,洛克通过对《圣经》的考据批判了“君权神授”的学说,提出了“自然”和“理性”两个概念,由此延伸出了以“自然法”和“个人意志”为两个核心原则的“社会契约论”。尽管有后世学者认为洛克的《政府论》是在“光荣革命”之前就已经完成了,但毋庸置疑的是,《政府论》对整个18世纪的西欧以及美国宪政制度都产生巨大影响,“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洛克的思想风行整个欧洲大陆”。
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大多深受洛克思想的影响,抑或可以说洛克的思想主要通过他们得以广泛传播。笔者在此无意对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法国的思想家们进行阐释,《剑桥十八世纪政治思想史》的著述者们就此已经有了详尽的论述,很难有人望其项背。他们对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以及以狄德罗为代表的百科全书派等启蒙运动时期的学者们关于政制的讨论作了较为全面的评述。在法国的历史上,18世纪是一个“革命世纪”,它的标签自然是1789年的大革命,芬纳称“法国大革命是和以前整个生活模式的决裂”,“法国大革命动摇了整个社会”。18世纪之所以被称为革命世纪,不仅仅在于大革命的发生,此前就已经开始的启蒙思想家们有关政制的论争也应该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提出的有关现代政制的理论,为西欧现代国家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法国大革命时期国王被送上了断头台,标志着千年封建制度的终结,共和政体的建立开启了政制的现代化,开始探索建立一个合法的为大众所能接受的政府形式。1789年颁布的《人权宣言》通过强调启蒙思想家们强调的“自然权利”(ius naturae)否定了封建的等级制度,从而进一步消除了教会的和贵族的政体模式。卢梭于1762年出版的《社会契约论》中提出的自然权利和主权在民的思想,更是在《人权宣言》中有所体现。《人权宣言》中提出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体现了启蒙思想家们提倡的理性,理性体现的是个人意志,而政府的合法性则是建立在“意志”观念的基础上的,即同意或者是认可的原则。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只有在政府保障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和自由的前提下,民众才会表示“同意”,这个政府才是合法的。拿破仑时期颁布的《拿破仑法典》(Napoleonic Code)进一步用法律的形式确认了启蒙运动时期提出的保护私有财产、平等和自由等原则。
在德意志的政治传统中,“君权神授”的神学政治理论根深蒂固,是君主专制的理论基础。专制制度起步较晚的德意志邦君们,“遇见”了法国的启蒙运动,普鲁士的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与伏尔泰相交20余年之久,闻名遐迩的数学家、哲学家达朗贝尔(Jean le Rond d'Alembert)是弗里德里希二世宫廷里的座上客。在弗里德里希二世执政时期制定的政策深受启蒙运动思想的影响,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无论弗里德里希二世还是其他的邦君们在制定他们的政策时都是选择性地接受了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首先,集权的邦君们逐渐地摈弃了“君权神授”这一神学政治理论,接受了以个人意志为核心的“社会契约论”政治观念,以社会中个体认可的政治的合法性取代了中世纪以来一直实行的君权神授的神权政治,这是开明君主制最基本的理论基础。在芬纳看来,“启蒙思想绝对不是民主的”,因为启蒙运动的精英们并不相信大众可以自谋其福,更何况原有的城市议会、行会,以及等级议会和教会依然在束缚民众的自由;因此,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都把希望寄托在君主身上,“君主越活跃、越专制,启蒙思想家实现蓝图的机会就越大。因此,他们倡导最为极端的专制,即‘合法专制’或‘开明专制’”。这种现象似乎在德意志表现得尤为明显;这是因为掌握权力的君主把符合他们统治权术的启蒙思想付诸实践。弗里德里希二世在执政时期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把社会契约论中保护自由和私人财产的内容落实在了他制定的法律中,促进了司法机构和法律的系统化和合理化。如果说法国是以暴力的大革命的形式走向了现代国家,那么德意志则是通过在邦国中进行的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实现了国家的现代化。
17世纪初,英国殖民者开始移民至美洲大西洋沿岸,直至18世纪中叶逐渐形成了13个英属殖民地。虽然美洲大陆远离西欧大陆,但依然与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的思想自然也不远万里传到了美洲大陆。在美洲没有像西欧大陆那样的世袭贵族和教会贵族,因而没有可能建立起贵族政体;也没有西欧大陆的政治传统,因而也不会受保守传统的束缚;在移民美洲的殖民者中不乏角逐权力的政治家,他们虽然没有像哲学家一样创造新的理论,但是却能在这片新的土地上实践启蒙者提出的政治理论;所以,“启蒙思想在美国比在欧洲得到更为充分的实现”。18世纪中叶,13个英属殖民地联合起来反抗宗主国的经济政策,引发了争取摆脱宗主国控制的美国独立战争,为说明战争的正义性发布了《独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这个宣言中有选择性地接受了西欧启蒙思想家们的各种观念:自然权利、社会契约、自由、平等、三权分立等,可谓集启蒙思想的大成。正如芬纳所说:“德国和法国是启蒙之火燃烧得最为璀璨的地方,而美国革命则体现了最为纯粹的启蒙精神。毫无疑问这是欧洲人所梦寐以求的,但是由于一方面是世袭贵族,一方面是根深蒂固、富可敌国的教会,这种精神在欧洲不可能实现。”《独立宣言》以及此后的美国制宪会议(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的政制模式又反馈到欧洲大陆,成为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模板。
美国的政制形态源自西欧,或者更确切地说源自英国,在实践启蒙运动思想的过程中又有了自身的特征和创新,由此开创了有着“美国起源特征”政府体制。在美国政府体制的影响下,西欧各国完成了现代政府的形态建构。
(摘自《欧洲文明进程·政府卷》第405—4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