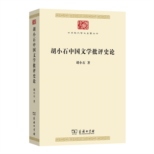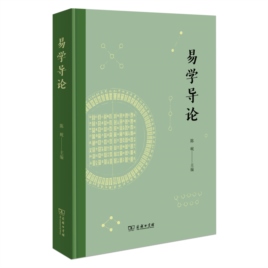在朱熹列入《周易本义》的九幅易图中,首当其冲的便是《河图》与《洛书》。“河图”的“河”, 专指黄河;“洛书”的“洛”,专指洛水。“河图”和“洛书”这两个名字,并没有出现在卦爻辞中,而是出自《系辞传》:“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按照《系辞传》的记载,在伏羲氏创作八卦之前,从黄河中出现了“河图”,从洛水中出现了“洛书”,伏羲受此启发,从而画出了八卦。
除了《系辞传》之外,“河图”与“洛书”还在《尚书》《论语》《礼记》等很多种其他的先秦时期的古文献中出现过。比如《尚书·顾命》篇中就有“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之说,根据这种记载,“河图”在被人发现之后,就被作为重要的物品进贡给了帝王,并且被当作珍宝,与大玉、夷玉、天球这样一些奇珍异宝一起被收藏了起来。
从《尚书》的记载中,我们虽然可以确信,“河图”是一个非常珍贵、重要的东西。但《尚书》的记载却有一个跟《系辞传》一样的问题,那就是没有明说“河图”“洛书”究竟是什么?比如说多高、多长、多宽,长什么样子,上面有没有文字或者图画?这些问题的答案,就现有的文献来说,我们一无所知。......
被朱子放到《周易本义》中的《河图》和《洛书》,是两幅以黑白点为主要元素,以数字和方位为主要内容的图像。
在《河图》中,从一到十的十个“天地之数”,被以两两一组的形式,安置到了东、西、南、北、中这五个方位。我们之前学过,在《系辞传》中,一、三、五、七、九是“天数”,二、四、六、八、十是“地数”。按照朱熹的解释,在天地之数中,一、二、三、四、五是“生数”,各自按照所属的方位,生成金、木、水、火、土五行;而六、七、八、九、十则是“成数”,一一与“生数”相配。具体来说,天一生水,位居北方,地数六与之相配,共同居于正北方;地二生火,位居正南,天数七与它相配,同居正南;同理,天三生木,与地八共居正东;地四生金,与天九共居正西;天五则生土,与地十共同居于正中。这样一来,《河图》就实现了天数、地数与五行、五方的整齐对应。
而在《洛书》中,则引入了九宫的形式。坐镇中央的是五,位居正东、正西、正南、正北的,分别是三、七、九、一,位居东南、东北、西南、西北的,则依次是四、八、二、六。《洛书》最为巧妙的地方就在于,不论是横着、竖着、斜着,只要把任意三个数连成一条直线,那么这三个数的和,就一定是十五。
不过,这两幅图虽然都非常精妙,但从《系辞传》《尚书》《礼记》等文献的记载中,我们完全看不出这两幅图跟“河图”“洛书”之间有什么关系。那么,为什么朱熹要把这两幅图,当成《河图》《洛书》,放到《周易本义》中呢?这是因为,在宋代学者看来,既然《系辞传》说《河图》《洛书》是伏羲创作八卦的灵感来源。那么,在《河图》和《洛书》之中,一定蕴含了一些精深高妙的道理,只有这样,才能匹配它们作为《周易》理论来源的地位。
带着这样一种问题意识,北宋时期的学者们,就开始尝试着绘制《河图》和《洛书》。在这一过程中,数理变化和方位坐标,这两个既有易学维度的理论意义,又跟现实生活密不可分的元素,就成为重点。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两幅图,也就这样被画出来了。至于说这两幅图的作者是谁,历史上是有争议的。有人认为是“希夷先生”陈抟,有人认为是宋初学者种放,但根据现存的历史文献来看,这两幅图最早出现在北宋时刘牧所写的《易数钩隐图》中。只不过,在刘牧的学说中,《河图》《洛书》的内容与朱熹的版本却是相反的。“天地之数”五十五点图是《洛书》,“九宫”范式的四十五点图才是《河图》。
虽然《系辞传》中把《河图》和《洛书》都作为八卦创作的来源,但历史上也有一些说法认为《河图》跟《周易》的原理更密切,《洛书》则跟《尚书》的理论更接近。比如刘勰在《文心雕龙》里就说:“河图孕乎八卦,洛书韫乎九畴。”意思是说,伏羲看了《河图》,然后画出了八卦;大禹看了《洛书》,创作出了《尚书·洪范》篇里面治理天下的“九畴”之法。
朱熹之所以对调了刘牧的《河图》与《洛书》,也是受了这种说法的影响。在他看来,五十五点图,由从一到十的十个自然数构成,这与《系辞传》中的“天地之数”完全一致。所以,五十五点图应该是“天地之数”的理论来源,与《周易》更加契合,应当是《河图》。而四十五点图,按照九宫格的形式,由从一到九的九个数构成,与《尚书·洪范》篇的“九畴”正好对应,所以应当是《洛书》。由于朱熹在历史上的影响太大,在南宋之后,我们所看到的《河图》和《洛书》,就基本都是朱子对调后的版本了。......
随着朱熹把黑白点范式的《河图》《洛书》放进了《周易本义》之中,《河图》《洛书》从一种颇具神秘性的祥瑞,变成了两幅以“天地之数”和“九宫之数”为主要内容的黑白点图像,我们必须认识到,在此之后,“河洛”对于易学的意义,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