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编辑推荐
生动清晰呈现博物馆人类学学科史脉络
《物与他者》是“博物馆人类学名著译丛”第一本面世的图书,以博物馆人类学学科史研究为脉络和主旨。
博物馆人类学研究在用人类学理论观照和指导博物馆实践,以及在博物馆里开展人类学研究这样两个维度上展开理论探索,对于当代中国的博物馆事业发展,具有无限丰富的方法论意义和工具性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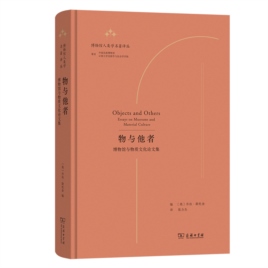
定价:¥66.00
生动清晰呈现博物馆人类学学科史脉络
《物与他者》是“博物馆人类学名著译丛”第一本面世的图书,以博物馆人类学学科史研究为脉络和主旨。
博物馆人类学研究在用人类学理论观照和指导博物馆实践,以及在博物馆里开展人类学研究这样两个维度上展开理论探索,对于当代中国的博物馆事业发展,具有无限丰富的方法论意义和工具性价值。
《物与他者》全面呈现19世纪中期以来博物馆人类学的发展,是博物馆人类学研究不可回避的必读性书目,对人类学、博物馆学、历史学等人文学科研究者有重要意义,在博物馆、艺术、物质文化与多元文化领域也具重要价值。
这本书讨论与博物馆史和物质文化有关的人类学关键问题,如博物馆陈列与人类学理论之间的复杂互动;人类学研究与公众教育之间的张力;博物馆民族志对于美学实践的贡献;人文主义文化与人类学文化的关系;民族志器物与纯艺术之间的关系;以及最根本的,物与文化表征的问题。
博物馆作为一个物质性档案,在物质性的三维以及时间/历史的第四维之外,还存在第五个维度。由于博物馆中的物曾经属于“他者”,那么一座博物馆的形成必然隐含着某些我们可称为有关“权力”(power)的关系:在特定的空间、时间和意义背景下,将某物从某行动者手中“征获”(expropriation)——不仅在这个词原本的抽象意义上,有时也在那些更不堪的、更接近“盗取”和“掠夺”的意义上——并由观者在另一种背景下进行挪用或占有(Foster 1984)。然而,对于观者而言,这种“占有”的权力是外在的,因为她/他既不是所看之物的实际“拥有者”,也无从决定以何种形式对其进行再语境化。诚然,个体的再语境化过程的确存在,但这些经过再语境化的物也可以对其观众产生影响——这种力量并不是物所固有的,而是由博物馆这个在特定历史社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机构所赋予。
这个有关“所有权”的问题反映了博物馆作为物质性档案的第六个维度:财富(wealth)——尽管有些人可能认为这只是权力维度的一个方面。在纯粹的经济学意义上,物质文化一直是某种“文化财产”(cultural property),甚至在现代民族主义的政治进程将其这般定义之前便是如此(参见Handler的文章)。物质文化的物质属性使之与西方获取和交换财富的经济过程纠缠在一起。尽管民族志材料中有许多是征获所得,其中并不涉及交换,但也有许多来自交易或购买,因此博物馆藏品的发展一直严重依赖于个人、法团或国家财富的投入(参见Chapman和Stocking的文章)。虽然贝丘的碎屑从未被赋予与其发掘所花费的劳动相称的价值,但相较于其他更具“文化”价值之物,它的美学-经济价值,一直是影响对其进行收集和保存资源配置的一个因素(参见Hinsley的文章)。从一开始,市场过程(market process)就对作为物质文化档案的博物馆的形成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尤其是博物馆藏品被视为,或逐渐被视为艺术品而非普通器物(参见Wade的文章)。
这也引出了另一个更为深入的定义博物馆的维度,也是本文将讨论的最后一个纬度:审美(aesthetic)。尽管非西方民族的物质文化在历史上被排斥在专门的纯艺术博物馆之外,并且在普遍的人文主义或进化论视角的美学标准下遭到贬低,但自其最初进入博物馆以来,也经历了一个审美化(aestheticization)的过程。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西方审美标准的相对化(和普遍化)造成的(参见Williams的文章),同时,也与传统物质文化生产的种种“再语境化”过程有关。那些曾经具有多种功能的器物,其美学元素一旦被抽象出来,其他功能经常在文化涵化(acculturation)的过程中逐渐削弱,其中的实用功能转移到了西方技术产品上。只要传统物质文化还在继续被生产,其审美就会被从本土和西方的角度进行重构——无论是作为媚俗的古董(curio kitsch)还是纯艺术(fine art)。因此,在传统背景下通常具有精神价值的“物质文化”被“再精神化”(对西方来说),成为审美对象,同时也受制于世界艺术市场的进程。随着他们的作品被卷入市场关系,一些曾经是或可能是本土工匠的人转变成了西方意义上的艺术家。但是,无论被定义为“变形的艺术”(art by metamorphosis),还是被创造成“指定的艺术”(art by designation),那些曾经作为物质文化进入民族志博物馆的物品如今已经完全有资格跻身艺术博物馆(Wade and Cannizzo 1982: 10)。
正是在这些有关博物馆定义的讨论中——从词源学和历史两方面——本书收录的博物馆人类学史研究,虽以机构为关注重点,也的确具有更广泛的理论意义。
京ICP备05007371号|京ICP证15083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1884号 版权所有 2004 商务印书馆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1884号 版权所有 2004 商务印书馆
地址: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邮编:100710|E-mail: bainianziyuan@cp.com.cn
产品隐私权声明 本公司法律顾问: 大成律师事务所曾波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