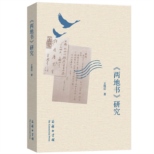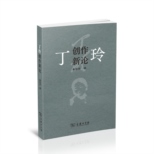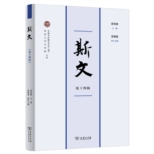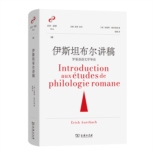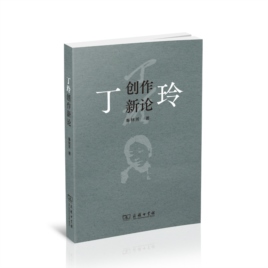显示全部编辑推荐
在“两种文学传统的影响”下,丁玲的创作矛盾和思想如何凸显其普遍性?
打破丁玲研究窠臼,提出众多新创见和新思路,带你以新的视角重看丁玲创作。
1.丁玲研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一门“显学”。出版的相关著作较多,有以著作形式出现的传记批评,与此相关联,还出版了十多部专题性的传记类著作,这些著作以对史料的挖掘和梳理见长,但因体例所限,对丁玲创作的评析还不够。本书从宏观上将丁玲置于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中,细读丁玲作品文本,研究视角较新颖,或可填补出版空白。
2.本书作者秦林芳先生深耕丁玲研究领域二十余年,所提观点富有新意,且受到学界关注。本书中多篇章节已经发表,并被多次转载和引用。
3.本书小开本平装,封面烫白、烫黑工艺,方便握持阅读。